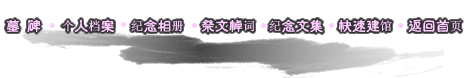与父亲的“战火”,因母亲燃起。
是不是天下父子的关系都这么别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儿时从未见父亲与他的父母亲说笑过,如今对我这个年过半百的儿子不苟言笑不说,还十有五六地不顺眼,生活中许多步调均不在一个频道上,用他的话说,显得总是那么的拧巴。集中表现在与我们一起生活后,对待母亲的照料上。
父亲已八十有五,大多父母在孩子眼里都是“劳苦功高”的。早些年我就提出,他们七十岁后就来与我们一起生活、让妻辞了职专事照料、好好安享清福的意见。可他们坚决不肯,说能跑能动还不到麻烦我们的时候。直到2023年2月母亲开始血液透析、8月又摔跤骨折瘫痪在床、恰巧我家斜对面就有医院,才迫不得已在我这里住下来。父亲说,父母的家是儿女的家,儿女的家不是父母的家。这话咋听起来似乎有些哲理,但却十分的扎心。儿时一大家三四代人住一起热热闹闹的情景历历如在昨日,实在不愿信社会物质丰富了人伦道德却沦丧了的邪,一家人都不能和睦共处,何谈立数十亿多人和谐社会的正?果然妻子不称我心,去年都办退休了却退而不休,只因父母没有松让她辞职回家的口,她乐得置身事外。退休了的姊妹也一样,偶尔来照顾一下可以,要专来守着伺候不许,将“两人相互照料、一人不行了另一人照料、两人都不行了或最后一人不行了再由子女照料”的“居家养老观”坚持得死死的。我因为工作忙不能全身在家,妻子和姊妹都退而不休,母亲的吃喝拉撒医护主要就落在父亲肩上。可父亲毕竟年事已高,难道要等他也倒下了才是子女出手的时候吗?对此,我与妻子进行了反复的、长期的、严正的交涉,只因父亲不放手、不协作,没几天她就别扭得又上班去了。这还不是问题的要害,要害是在对待母亲养护的细节上,我与父亲从此拉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比如关于母亲假牙管理问题。我主张每天晚上清洗后用淡盐水浸泡,而且要用温开水,他却是冲一次水泡好几次,等我发现水浑浊后方知端倪。比如关于更换和清洗尿布问题。不说那么多吸水性能好的布料不用却用破烂晴纶作尿布,单说洗尿布多不打肥皂洗衣粉,后来置办了一次性尿布尿裤,用了不愿扔还要晾干了重复再用,而这样的尿布接续晾满房间,就可想而知房间味道了。我们有时偷偷将用过的一次性尿布尿裤扔了,他到处寻找并能从垃圾筒中翻出来,声高脸恼得不行。比如关于用自动起身床问题。去年下半年母亲坐不稳了,吃饭都需要人喂,我们不在父亲要扶她坐起就很吃力,就干脆躺着喂饭、看电视、会客,可总躺着怎么行呢?便与他商量购置个自动起身床,可用了两三天就让撤走,理由是床位高出三四公分,他给母亲按摩不方便。我再三而不能说服后,只好将床撤下。有次又换了上去,他生气得训我,说我总是和他对着干,不得已搬放在了客厅窗台。放到客厅大窗台,一是当床用,来客住不下可应急;二是找机会,主要是以我人为的示范,试图对父亲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晚上我专门躺在上面看电视,待父亲经过时故意将床按起,然后对妻子说:“看怎么样?”妻子故意惊讶地回应:“还真是方便哟!”。后来不知是鼓动妹子还是我姨做工作,才同意又用上,可母亲已查出腔梗,逐渐说不出了话,咀嚼困难改吃了流食,左臂左腿也浮肿了。这只是“战争”的局部,从怎么吃药、如何吃饭,到擦屎擦尿搬挪洗涮;从一次吃饭的量,到喝牛奶是稀好还是稠好,“战火”全方位在我父子间燃烧,经常是我说这样好,他偏说那样好,我这样摆置了个东西,一转身他就换成了别的,有时甚至争执到互不相让,把两人都气得够呛,常要妻子赶来当和事佬。
母亲好着时,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就能体现出绝对“权威”,现在说不出了话,看人都不带眨了眼,随时都可能走人,面对夫与子围绕她起的“战火”,不知她的心中还有知觉否?舅、姨和姊妹多次从中协调,家里交我和妻子做主,让他少管事,他却说你们能彻底管,能让他完全放手他就放——看来他是不放心把母亲交给我们。我们没人敢拍这个胸膊,我因此对妻子有了很大的意见,她将我们谈恋爱时我给她提的要求忘到脑后去了。我建议至少双休日晚上由我或妻子陪床,姊妹来了也可让她们陪,能换他到小房间清静些许,几次以为默认了,可到晚上却不执行,实在是“犟”老头。抖音上一个名叫“悦纳”的人,将照顾九十多岁母亲的日常及感悟常传上去,其耐心和胸怀很是叫人敬佩。我与父亲这么地拧巴,是我真的是同事眼里的“直”人和妻子口中的“犟”人吗?与这位“愉悦地接纳现实”比,可能是我的修行还不够吧。因照料母亲与父亲争来斗去,也许是上天给我中年人生安排的又一场修行吧。现在的许多孩子与父母不住一起,不知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不住一起还能算一“家”人吗?我的思想与父亲不同,看来与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同。但这一现象却说明,“矛盾”原来也是可以通过“回避”来“解决”的。呜呼奈何,奈斯若何。
父亲是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人,能自己干的事从不叫帮手,更是一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人,总寻着买便宜东西,上街再饿也很少下馆子,退休后又多干了15年之久,彻底不上班后便包揽了几乎所有家务。搬来我这里后,除让他陪母亲透析、盯着母亲吃药和做他俩的午饭外,其他一概不让他管。可我和妻子下班回来,一家人的晚饭做好了。双休日早晨妻子一不留神晚起了几分钟,他已在厨房忙活起来。说好脏衣服统一周末洗,可到周末洗衣机中滚动的,永远没有他们的衣物,因为父亲随手都洗了。馍吃完了,妻子计划晚上回来蒸,可回来蒸好的馍已凉在案板上。为尽量减少父亲受累,出门前妻子把和好的面藏在柜下,可等回来馍已上锅或已出笼。会计出身的他,做家务永远都讲统筹,水龙头下要接个盆,洗手脸的水要留着冲马桶;购物要挑时机,得了便宜会整回一堆,常将女儿也考虑在内;接了几箱特仑苏不开封,却要另买回便宜奶喝,登记了生产日期掐点以备走亲友用;蒸馍的同时必带了稀饭及红薯土豆南瓜甑糕之类。父亲做的稀饭,多是蒸馍顺带着蒸出来而不是熬出来的,炒的菜大多也不好吃,可妻子宁愿吃父亲的“省手饭”,也懒得晚上下班回来再点火,弄得我常常没胃口也不好去打击父亲的积极性。双休日有时不想做饭,想给他们买点“改样”饭来,我们也想在外面潇洒一下,可他大多不让,弄得我们有时也不好自己个去解馋。一天到晚围着母亲和这个家转的父亲,倒成了我们家的老“保姆”。
说起照料母亲,父亲堪称典范。除量血压、吃药、换洗尿布、做饭喂饭、陪透析等外,早晚各按摩半小时雷打不动,虽随母亲病情的变化会哭声哀腔甚至偶尔会声高脸恼,但多是月琴亲月琴棒地陪说陪笑,把年轻时欠的肉麻话一股脑都补上了。来我这里两年多了,没有一晚离开母亲的床,没有一天离开母亲的视线。我推母亲透析时让他去晚点,总是我前脚刚将母亲安顿在病床上,他后脚就跟到了。台前付款结账,床前按摩说话,中途不时进去看看,有时会去建国门老菜场买母亲最爱吃的板栗小包子,多不与人闲言,没事时就不声不响地在透析室候客厅干坐,一坐一个上午,去接母亲时常能见他独坐沙发打盹的样子。父亲对于母亲的好,让妻子很受感动,说父亲是母亲一生最大的“福”,让我要向父亲学习。
父亲和我都是母亲至爱,缘何我俩因母亲而尖锐了矛盾?以我之见,除了生活理念外,核心有二,一是用人,二是节俭。父亲只知自己动手,不会调动和发挥周围人的能动性。在生活压力这么大、节奏这么快的社会,要想靠别人自觉还能事事做到心坎上,何其难哉,快捷办法便是学会用人。可他历来不愿麻烦人,不麻烦人是美德,但另一个极端却是——拒绝交往、拒绝合作、拒绝帮助,如此便降低了成事或成大事的机率。潜在到子女管教上,不用子女干这,不用子女干那,岂利子女成材?岂利责任心养成?长此以往晚辈对于长辈的孝心还怎么尽?而父亲的节俭,更是令我心痛,比如一次性医用口罩用完后,还要放到卫生间当手纸用,而且还要一剪两半用,林林总总,无处不见他省吃俭用的痕迹。要知道,他有六七千的退休金,母亲也有两千多养老金,两人都这把年岁且母亲都这样了,还想攒下钱接济儿女怎么着?让人甚是心疼和不安。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可在其他事情上我可以让步,在照料母亲问题上我不愿退让,这是“战火”之所以能燃起来的根源之一。
母亲在,与父亲尚如此拧巴,母亲要是走了,不知还会怎样?但以目前各自的认知看,如果双方都不退让,这样的“战火”可能不会轻易熄灭。父亲能坚持自己的主见,并底气十足地与我们争长论短,反想起来倒不是件坏事,说明他思路清晰、身体健康,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战火”倒是不要熄灭的为好。
又一次争执后的午休,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骑在父亲肩上,走在雨后黄场村东的打麦场上,电房扯出的电线上站着几排小燕子,空气是那样的清爽。
一转身,母亲出现在村口,戴着草帽,穿着花衫,招手喊我们回家吃饭。
2025年5月4日于1321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