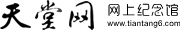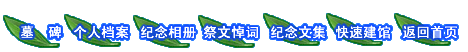一.名门闺秀
我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母亲的爷爷是清朝举人,当过全州知事。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自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十四岁就考上了清末公派留学生,就读于日本著名的帝国大学。外公去日本的时候,根本不懂日语,临出国之前才突击了两个星期,轮船上又学了几天,就靠这点日语进了日本帝国大学听课,四年之后居然以优异成绩与日本同学一道从帝国大学毕业。
外公学成回国,先在济南大学当教授,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第一批大学教授之一,娶了一个山东的大家闺秀做我的外婆。后来又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民国十六年,应时任广西省长的马君武博士之邀,回广西举办广西大学,出任广西大学教务总长兼教授。
民国十八年,我母亲四五岁的时候,外公于暑假携全家乘船从梧州沿水路返回老家全州,在蒙山遭土匪打劫,全家被绑。说来也冤,土匪原来打算劫持的并不是我外公,而是外公的兄长,时任广西省参议会议长、两广财政厅长的蒋继伊。蒋继伊大我外公七八岁,曾中清末举人,并同时与我外公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从政,也是广西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连蒋介石都尊称其为“叔”。我外公蒋继尹,名字与蒋继伊仅仅相差一字,不,仅仅相差两笔,不但字形相似,连读音也相近,极易混淆,加上土匪文化程度不高,于是阴差阳错抓了我外公全家。谁说名字不影响命运?这就是一例!
土匪以为抓住一个两广财政厅长,可以换回大把银子,谁知道抓的只是大学教授,好不气恼!土匪眼中的大学教授不过是不值钱的穷书生,但这位穷书生好歹有个两广财政厅长的亲哥,想必多少也能诈回一些银两,于是把外公一家扣为人质,要挟蒋继伊拿钱赎人。蒋继伊与土匪多次谈判,还不容易将赎金由一万大洋降到了四千,却不料掌管广西军政大权的李宗仁、白崇喜不肯答应,认为用钱赎人是助长了土匪的气焰。李宗仁与白崇喜行伍出身,只知道用枪杆子说话,立即派了军队前去围剿。大兵压境,土匪被逼“撕票”,外公一家的男丁,几乎全部惨死在土匪刀下。说是“几乎”,那是因为母亲的大哥、我的大舅命大,脖子上被土匪连砍三刀,昏死过去,土匪以为死了,没想到他居然死而复生,从死人堆里爬了回来,后来一直活到八十六岁,但从此落下了歪脖的毛病。还有一个男丁——我的小舅,是在襁褓中吃奶的婴儿,也免一死。土匪也有土匪的规矩,只要钱能到手,绝不“撕票”;钱不到手,就别怪他杀人不眨眼,但只杀男丁而不杀女眷,所以外婆与母亲得以死里逃生。做为大学教授和两广财政厅长亲弟的外公竟被土匪“撕票”,成为当时轰动整个广西的一大要案。
外公不幸英年早逝,母亲家中日益没落,但也没有耽搁孩子的前程,母亲曾在桂林女中读书,是女中有名的校花。后来,母亲不知什么原因去读了“桂林俄专”。那时候,父亲还没毕业,就在俄专当了助教,并深受学生欢迎,母亲就是当时崇拜父亲的学生之一。所以,我父母亲的结合也可以说是一场“师生恋”。 母亲是典型的百里挑一的美人,追求母亲的人自然很多,可是母亲与外婆偏偏就看中了家境贫寒的父亲。
有一次,父亲得了伤寒,就住在母亲家中,那时候父母亲的婚姻关系还没有正式确定下来。伤寒在当时是人人谈虎色变的恶疾,父亲也差点因此丧命,连看病的郎中都说生死由命了。母亲的家人也不同意这样一个像女婿又非女婿的病人住在家里,多亏母亲与外婆一再坚持,才让父亲在母亲家中慢慢康复起来。每每谈及此事,父亲总是感激涕零。
抗战时期,母亲逃难到了重庆,到重庆中央政府印钞厂当了一名女工。从俄专出来的人大都受过苏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少能够安分守己,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出头,母亲又积极参与组织了一场“反迁厂”大罢工,并被工人们推举为与厂方和政府谈判的“代表”。大罢工的起因是抗战胜利,国民党中央政府要迁回南京,专门为政府印制钞票的印钞厂也要跟着搬迁,原来在印钞厂工作的重庆当地的工人就要丢掉饭碗,于是通过大罢工来“反迁厂”。至于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政治目的?母亲没说。大罢工迫使厂方和政府做出了很大让步,因迁厂被辞退的工人每人都得到了一笔不小的“安置费”。“反迁厂”大罢工胜利之后,罢工工人为了感谢我母亲,专门打制了一块“罢工胜利”金牌送给我母亲,可惜为了筹措去解放区的路费,母亲把它给卖掉了。自那以后,她就与我父亲在我大伯的资助之下飞往了东北阜新,并在阜新生下了我。不久,就和父亲与一帮革命青年一道,投奔到华北解放区去了。
从“蒋管区”到解放区,路上要通过好几道国民党部队的关卡,我父亲扮作生意人,母亲装作阔太太,其他人分别扮成挑夫与脚力,一路蒙混过关。母亲天生丽质,从小就受书香熏陶,又受过高等教育,装作阔太太毫无破绽,对付哪些只知道阿谀奉承、见钱眼开的兵痞,自然绰绰有余,一路为我父亲他们减少了不少麻烦。
母亲虽然是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但是到了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其前身就是有名的“抗大”)之后,脱胎换骨,随军南征北战,飒爽英姿不让须眉。朝鲜战争爆发,母亲几次主动要求参军,如果不是家庭出身“地主”(我就不明白了,外公的大学教授怎么就成了“地主”?),政审不过关,早就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去了(如果真去了,三弟、四弟他们恐怕也就没了)。
母亲也在国家统计局当过苏联专家的俄文翻译。回到桂林以后,当过桂林植物专科学校的政治教师和政教处主任。学的是俄文,教的是政治,而且教得比正规科班出来的还要好。政治本来是最枯燥的一门课,我母亲偏偏把它上成了最受欢迎的一门课。我真想象不出她是怎么改行过来的。我曾经问过母亲,母亲回答说:“我其实很少教他们什么政治,而是在教他们怎样思考,怎样做人。”母亲非常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学生都愿意与她谈心、交心,很多成为她的知心朋友。现在母亲已经离休三十多年了,每年还有不少学生专程到家里来看望她。
二.文革受辱
WG是个岁月疯狂的年代,荒唐到举国上下都用一个思想思考、都用一个声音说话、都用一个鼻孔出气,谁要是稍微偏离一点这把被公认为真理的尺度,就会被视为异端,轻则挨批、重则挨斗,甚至夫妻反目、兄弟成仇。我曾看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跪在大街上,被她带着“红卫兵”袖章的亲孙子用皮带抽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一帮“红卫兵小将”还在一旁拍手叫好。奶奶据说是地主(儿子倒是解放军军官),十几岁的孙子强迫奶奶背“语录”改造思想,老人家年级大了,记不住,孙子就在大街上当众用皮带抽她,以示与“地主阶级”划清界线,真不知道这孙子怎么下得了手?他也不想想,没有昔日“地主阶级”的奶奶,哪来的今天当“红卫兵”的孙子?更不知道她儿子做何感想。“红卫兵”对自己的亲奶奶尚且如此,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就可想而知了。
母亲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第一个冲击,来自她的学生。那学生是当时学校里经济最困难的学生,他上学所用的被褥、衣服、课本、乃至伙食费,几乎全部来自国家补助与我母亲的私人捐助(国家补助实在太少了);他病了,我母亲亲自喂汤喂药,曾把他感动得痛哭流涕。这个学生毕业时成绩不错,我母亲千方百计把他留在了科研单位。可是没想到,文革一来,第一个起来“造反”、把母亲揪出来“批斗”的,就是那个当年母亲资助过的忘恩负义的学生。“批斗会”上,那个翻脸不认人的“白眼狼”,为了表示对母亲的极大愤慨,用尽全身力气给了母亲当胸一拳,打得母亲顿时跌倒在地,半天喘不过气来,差点命丧黄泉。母亲从此落下了胸口疼的毛病,仿佛时时提醒她文革所受的羞辱。十年浩劫之后,“白眼狼”又到母亲面前痛哭流涕,一脸无辜地乞求母亲原谅,声称他当时是迫于无奈,急于想在众人眼里表白他并非母亲的得意门生,否则连他也要受到牵连。母亲原谅了他。我却难以释怀,担心“狼”总是要吃人的。
母亲的罪名呢?其一,因为她出身“大地主”,不是一般的地主,而是“大地主”,爷爷是清朝官僚且不必说,父亲虽是大学教授,却也置有几十亩田产,富甲一方(然而,外婆和舅舅他们变卖家产暗中资助共产党桂北游击队的“功劳”却没人提起);其二,因为她是父亲的夫人,父亲抗战时期当过国民党中校(抗战有罪吗?更何况父亲当时还是地下党推荐去的),母亲理所当然就是“伪军官太太”(“伪军官”这个词太难听了,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是为日本人效劳的汉奸走狗呢);其三,她给学生上过政治课,多次引经据典地提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因此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时也是学生必读的书籍,大家都可以引用,为什么母亲就不行?);其四,上世纪六十年代天灾人祸困难时期,她把口粮省下来让给学生,宁肯自己饿肚子也千方百计让学生不至挨饿,地主小姐会有那么好心吗?明显的是“收买人心”;……。呜呼,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今天看来,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也算的什么“罪状”,真叫人匪夷所思。可是在当时,哪怕是一句对伟大领袖不恭不敬的话,都有可能置人于死地,母亲的“罪状”就更加“十恶不赦”了。
学生的“揭发”,只是导火索,一场酝酿已久的“报复”终于爆发了。中国人天生就有一种“仇富”的变态心理:父母亲的级别与工资,在当时是凤毛麟角,是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也是周边单位中最高的,早就有人愤愤不平;父母亲养尊处优的生活,也令许多人望尘莫及,惹来不少不满的私下议论。现在机会来了,可以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
挨打、挨骂、“劳动改造”毕竟只是肉体上的痛苦,忍一忍也就过去了。难过的是灵魂上的痛苦,当时有篇社论说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岂止是“触及”?连做人的一切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起码的人格与尊严也全都丧失殆尽!言论受限制、自由受限制、读书看报受限制、活动受限制、食宿受限制,有一段时间,甚至连大小便也受限制;还要三天两头遭受群众“批斗”。任何“被管制”的对象,在每个“自由民”面前都必须点头哈腰、低眉顺眼,仿佛他们永远有赎不完的罪,仿佛所有的“自由民”都是他们的“上帝”,都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更可怕的是,谁被管制、谁自由,没有任何客观规则、没有一根公正的准绳,完全由当权者凭个人好恶、或者心血来潮说了算,当然借口绝对是冠冕堂皇的。
不过,比较起父亲,母亲的处境稍微好一点。至少,她还可以带着刚刚上小学的五弟一起住在“劳改队”集体宿舍(所谓“劳改队”,实际上就是单位自己私设的“公堂”与“监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却掌握着本单位职工的生杀大权),带着五弟一起吃集体食堂的饭菜,起码是“衣食无忧”。那个最小的还不太懂事的儿子的存在,使得那些想对她动手动脚的“造反派”不敢太过于放肆,使得她在烈日下、寒风中“劳动改造”时还有盼头,一再打消了她试图一了百了的念头。
最让母亲不习惯的是,尽管家已经被文革弄得支离破碎,她还必须得操持家务,毕竟身边还有一个需要照顾的小儿子。父母亲自开国以来,家中就一直雇着保姆。买菜、做饭、洗衣、带孩子这些生活琐事,基本上都交给了保姆,他们只知道一门心思做学问、不分昼夜“为党为人民”工作,从不知道如何安排家务、更不知道如何做家务。当时,母亲的工资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五六倍,父亲的工资更高,雇个把保姆根本不算什么(现在看来很平常,那时却很希罕。在中国,只要是希罕的事,要么就受到众人追捧,要么就受到众人排斥)。父母亲从来就不把保姆当外人,与其说是保姆还不如说是管家,不但同吃同住,而且连全家每月的生活费也都交给保姆,完全由保姆支配,安排全家的饮食起居。文革一来,雇用保姆也成了母亲的“罪状”之一。有人在“批斗”母亲时嘶声竭力地喊:“你这个地主、资产阶级臭小姐,解放前你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还没作够?解放了,你还想让劳动人民继续伺候你吗?……别做梦了!”喊喊也就罢了,还要母亲跪在地上向“劳动人民”磕头请罪,母亲不肯,几个“泼妇”上来就拽着母亲的头发,把母亲的头朝地上“彭!彭!”直碰,让母亲碰得头破血流才能解她们的心头之恨(“谁让你能请保姆,而我们不能请呢?”)!保姆被迫辞退了(其实保姆自己并不愿意走),从此,一切家务不得不全由我母亲承担起来。
所谓的“家”,也只是徒有四壁:书没了,因为这些书大多是古籍、西方文学与俄文书,宣扬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被没收了(可是,为什么连几十本俄文版的马列主义原著也被没收呢?难道读俄文版马列主义原著也有罪吗?);本来就不多的私人财产没了,因为这些财产引起了某些人眼红,工农兵都没有的财产,凭什么“臭老九”就应该拥有?二话没说,被查抄了;除了身边的小儿子,大一点的孩子都不在家了,该躲的躲了,该逃的逃了;家也不再是花园式的小别墅了,而是刮风透风、下雨漏雨、连普通工人都不愿住的“窝棚”。还有什么呢?除了破旧的床铺与被褥,就是一张伟大领袖像和他老人家的几条语录,……。当初,父亲和母亲就是为了追随伟大领袖的理想,才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想不到伟大领袖得了天下之后,他的忠实追随者竟然落到了这种地步!可悲可叹啊!
“文革”中还有一件“黑色幽默”事件,让母亲至今记忆犹新。请看母亲2007年82岁时亲笔所写的短文《文革琐事记实》:
四十多年以前,“文革”正热火朝天,我们早被赶出了教授别墅,全家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屋内,陋室中间用竹席草草隔为里外两间,内间作卧室,外间自然是厅,也是儿子的住处。按照当时“表忠心”的惯例,我们在隔席正中恭恭敬敬贴了一张毛主席像。
陋室所在之处老鼠特多,为防鼠患,家里还养有一猫,平时猫吃饱了就跳到里屋的床上睡觉。
当时我已被所谓的“革命群众”定为“历史反革命份子”、“伪军官太太”,被监督劳动改造,失去了人身自由。六八年的一天中午,刚刚劳动改造收工回来,只见厅正中的毛主席像被撕掉了,落在地上,顿时就把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那可是对“伟大领袖”最大的不忠与侮辱!心想这该怎么办?报告嘛,自己怎脱得了干系?不报嘛 ,万一是革命群众故意试探的呢?(后来想想,其实他们并不敢用伟大领袖的像如此乱搞,只是当时我确实被吓懵了)反正,已经习惯了老实交待,一念之差,竟把这要命的事如实报告上去了。
“革命群众”自然是如获至室,本来他们就无事找事,送上门的“罪行”哪里还肯轻易放过?谩骂、批斗、阴谋论立刻铺天盖地而来!让我有口难辩!狗急还跳墙,我一口咬定是那倒霉的猫干的。因为每天我都不关里屋的门,那天鬼使神差却把门关上了,猫进不去睡觉,于是从竹棚顶上的空隙跳过去,不想抓掉了像,而且像上有明显的猫爪痕迹。
这下非同小可,居然连桂林市公安局都惊动了。他们还算公道,并没有当下就把我拷起来,只要求照我说的把猫关在外屋,把主席像依原处贴好,看结果是否真如我说。当天下午,测试开始,我们躲在屋外,等最后“判决”的结果。天哪!此刻的我真是命悬一线!我的命竟攥在一只畜牲手里!多亏上天有眼,那猫也不负我养育之恩,竟然有板有眼,丝毫不差地重演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多悬啦!
最后,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文革之后,母亲当了图书馆馆长,是个说轻不轻、说重不重的工作。母亲如鱼得水,自得其乐。不但自己看了古今中外大量书籍,还经常借回来让我看,时不时还与我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那时,中国的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当务之急是物质生产,报刊、杂志、书籍这些精神食粮少得可怜,而且几乎都是千篇一律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东西,味同嚼蜡,根本无法填饱我那个饥渴、空虚的大脑。母亲给我借回来很多珍贵书籍,这些书籍今天看来很寻常,可在当时,大多数人连想都想不到,找也找不到,看就更看不到了。母亲给我借回的那些珍贵书籍,为我打开了探求知识的大门、打开了窥视世界的窗口,养成了我每日读书的好习惯。后来,我之所以能够在教育事业上小有作为,也得益于那些书籍给我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基础。
(初稿于2008-07-03,修改稿于2015-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