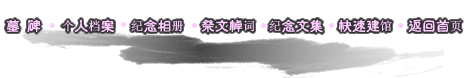母亲离开我们已经60个年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和许多记忆仍然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母亲中等身材,体态匀称,长方形脸,头上梳着发髻,穿大襟上衣和宽松的裤,裤脚用绑腿带绑着,显得干净利落,一双从小时候就被缠得只有约15公分长的尖尖的小脚,穿一双黑色小尖头布鞋。在我的印象中,母亲还是那样年轻,那样漂亮,那样慈祥,那样善良。
抱子唱歌 温馨时刻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大概五六岁刚有记忆的时候,秋冬季节,在她忙碌完一天的劳作,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盘坐在火炉旁,抱着我们轻声唱歌。虽然已不记得唱什么歌,但是她的神态仍记忆犹新--很舒心,很放松。
带我下地干活
在农村走集体化道路之前,母亲主要时间是在家里操持家务,但农忙的时候也会下地干活。我隐隐约约记得,春天播种时,母亲会下地帮父亲种玉米、点花生等,到秋天收割的时候,又下地掰玉米、收谷子……。农村实行集体化以后,地是集体耕种,社员按劳动记工分,秋后按家庭的工分分粮食。自这以后,母亲下地就成了家常便饭。我记得最深的是我上小学以后,母亲带我下地摘棉花。一大块棉花地里有几个女社员低着头在摘棉花。母亲用一块大方巾系成一个口袋,挂在我的胸前,让我把摘下的棉花放到里面去。她胸前则挂着一个大口袋。只见她两只手一左一右交替着同时摘,摘的很快,不大一会儿,胸前的口袋就摘满了,然后取出来放到地上的大床单上,接着又开始摘。我刚有棉花树高,也学着母亲的样子两手不停地摘,没过多长时间,我也摘得很快了,受到母亲的赞扬。母亲是摘棉花能手,是女社员中最能干的。晚上她带着我去我们院东屋的合作社小组记工分时,大家都围在大方桌的周围,桌子上点着一盏一尺多高的高脚煤油灯,我挤在母亲前面,趴在桌子旁边,看记工员在本本上记工分。工分是按摘的棉花多少计算,最高记10分,母亲总是女社员中摘的最多的,大概给她记的也是最多的吧!印象她总是乐哈哈的,大家也都是笑嘻嘻的。
母亲撇玉米也是能手。到了秋天,玉米熟了,男劳力负责用镰刀把玉米杆从根上割断放倒,女劳力和孩子们则或蹲或坐,在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一排排玉米杆上把玉米棒掰下来,扔到中间的空地上,傍晚收工时再用箩筐把玉米棒挑回去。母亲一般都是盘腿坐在玉米杆上往下掰,我负责把远处的玉米杆往她跟前送,她掰一会儿后,再往前挪一截,再坐下来接着掰。她掰得很快,我往往供不上她,一会儿地里就撇下一大堆。
纺花织布
纺花织布是母亲最拿手的手艺。
家里有一架纺花车,一台织布机以及纺花织布的相关用具。纺花车有一米多长,一米多高。织布机有二米多长,一米七八高,一米二三宽。都是用木头做的。
纺花织布工序繁杂,而且技术含量高,很多农户家里是没有织布机的。从地里摘下来的棉花到织成布,中间有很多环节。有几个环节给我的印象深刻。
首先,要将棉花拿到外村找人家的轧花机把花籽脱出来,再用人家的弹花机把棉花弹松软,卷成半斤左右的棉花卷。这是父亲的事。花弹好后,后面的工序则主要是母亲的了。接着,就是搓花条。撕下一块棉花,用高粱杆箭(高粱杆头上的一节)压在上面,就着凳子面或在腿上搓,搓成一尺左右的长条,俗称“花圪卷”,再把高粱杆箭抽出来,把棉花条放到笸箩里。然后接着搓。这道工序我们兄弟姐妹都帮母亲干过。棉花条搓出来后,就可以纺花了。纺出的线先是缠在线锤上,还需要用线拐子把线缠成一绺一绺的,一绺大概有二三两重。母亲坐在纺花车前,一坐就是大半天。
母亲的纺花技术很娴熟,她纺出来的线又均匀又细又光滑。这活只有母亲干,别人纺的线她都看不上。这和她上世纪40年代给共产党控制的边区政府纺线营生不无关系。我也学着试过,拽出来的线粗一截细一截的,不能用。
棉线纺好后,要给线上浆。用农村办红白喜事时才会用的那种大铁锅煮一大锅比较稀的白面浆糊,然后把棉线放进去用力搓,给棉线均匀地挂上浆。上过浆后,线就变得光滑了。一次大概能浆十来斤线。浆好后,捞出来拧干,穿在长长的浆线杆上,在院子里架起来,拿小擀面杖穿到每一绺的线中间,用力往下荡,直到把线荡直荡散,然后在太阳底下晒,直到晒干。这个活是力气活,大人小孩都可以干,我和我哥也帮着干过。
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做经线,一部分做纬线。
做经线的部分,要先缠在一个个能转动的细细的圆形器具(俗称”yuan”)上,然后在院子的两头各摆放一排十五个挂线的固定好的砖头,把那些圆器具yuan放在院子两头的中间,从其中15个yuan上把线拉出来合在一起,高高地举在手里,在院子里一边拽一边走,绕到两头的砖头上。照此循环往复,大概要走出400根线头来。走线除了技术,还需要体力,所以我们孩子都很乐意帮父母干,也是我印象最好玩,干得最多的活。
线走完后,就可以安装到织布机上去了。这个过程我印象不深,不知道是怎么安装上去的。只记得织布机的头上架着一个均匀地缠着厚厚的棉线,宽度和织布机相近的大经线轴,从经线轴上拉下来一层排列整齐的经线,绕过二三道固定在机上的横木杆,一根间隔一根地穿过吊在木框上方横木的两个zan(音),再穿过前面同样被上方吊着的xing(音),再前面就是织出来的布了。
zan是和经线轴等宽,高约30-40厘米,用打过蜡的布条或别的线材做成的像帘子那样的长方形线刷,两个zan的下方各通过两条绳连接两个踏板。踏下踏板,两个zan就形成一个高一个低,把400根均匀穿过两个zan的经线也就分成了上下两层。Xing在zan的前面,是和zan等宽高约10厘米中间竖向镶着400个小竹片,类似梳子模样的长方形木框,比较沉,从zan 出来的经线要有序地依次从每个缝隙中间穿过,和前面织出的布相连。
另一部分,就是纬线。纬线要先用缠穗杆缠成穗子做成梭心。缠好的梭心沾湿后放到梭子里,把线头从梭子中心的梭眼里抽出来才可以织布。经线和纬线安装好后,就可以织布了。经线从zan出来分为上下两层,再穿过xing,安装着纬线的梭子从xing前面的两层经线中间穿过,拉动xing用力挤压一下纬线,再踩动踏板,使两层经线上下交换位置,把梭子再穿过去。如此往复,便织出了布。
织布既是技术活,又是体力活。两只脚要一上一下不停地用力踩踏板,力度合适,速度均匀,两只手要一左一右不停地快速穿梭子,穿过去的线要又平又直,松紧适度,每穿一梭还要使劲拉动一下xing,把布织紧,眼睛还要时时盯着布面。织出来的布先是固定在一根类似长擀面杖的横杆上,织一小截,往下放一小截,最后都缠到下面的卷布杆上。因此,全身都得用力,很辛苦。记得母亲坐在织布机的尾部,双脚不停地踩踏踏板,双手轮换着操纵xing和梭子,布就织出来了。母亲经常是一大早就坐在织布机上,一织就是一天。
我十多岁的时候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在织布机上试过,不是梭子穿不过去,就是纬线拉不直,或者把经线挂断了。感觉要学会不容易,要学会整个织布的程序和技能更不容易。当然主要是我学得不用心,母亲大概对我也没有抱多大希望。母亲织出来的布,又薄又平滑,还给我们织出过白蓝相间的条纹布,即四五根白经线中间夹一根蓝经线。用这种条纹布做出来的衣服很好看,我和我哥都很喜欢穿。需要染颜色的,父亲就拿出去到染房去染。黑的,蓝的,印花的,各种颜色和花色的布都有。小时候,我们家铺的盖的穿的,都是母亲织出来的。
母亲对我两个妹妹,传授就用心多了,她们自己也学得认真,都成了纺花织布的行家里手。
过年更忙
母亲为了我们兄妹五个,一年到头总是忙忙碌碌的。尤其是过年,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一进腊月,就开始碾米磨面。那时不像现在的农村,可以用电动或水动机器,更不像城市,可以去商店买,而是要用由牲口拉着的石碾石磨去碾去磨。石碾石磨村里没有几台,要瞅别人的空。驴或马,要向队集体预约去借。碾出来的米,要用簸箕把糠一簸箕一簸箕簸出去,而且要碾三遍簸三遍;磨出来的面,也要用箩面的箩一箩一箩地把面箩出来,而且面也要磨三遍,才能把小麦里面的面粉都磨出来,因而也得箩三遍。可见,需要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再一个,就是给我们做新鞋新衣服。母亲每逢过年都要给我们做一身新衣服,新鞋。这也是我们过年最关心的。初一穿着新鞋新衣服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觉得很有面子,会很兴奋。做衣服,村里有一个裁缝,但我们小时候穿的中式服装都是母亲手工做的。母亲做的衣服很合身,很好看。挽的中式上衣扣,疙瘩小小的,硬硬的,别的大人看了都直夸。后来我们上学了,父母亲给我们做过几身学生服。父亲拿上布带我们到裁缝家里让人家量体裁衣,但做好后拿回来,还得母亲缝上扣子才可以穿。我们穿的鞋则一直都是母亲亲手做的。
做一双鞋从打褙,裁样,纳鞋底,缝鞋沿,到做鞋面,上鞋帮,做成鞋,需要好几道工序,好几天时间。经常是腊月三十晚上,我一觉醒来,还看到母亲在灯下赶着做活。我们大年初一早上醒来,枕头边总会看到新鞋新衣服。
临近春节前,母亲还要忙着蒸馒头、大糕,油炸圆馓、糖果、甲疙瘩,炖肉,剁馅等等,准备许多食品。这些食品或者供自家过年和接待亲戚客人用,或者供走亲戚作为礼品用。解放初期,农村由于受历史上长期封建迷信的影响,还残留着过年献山神,拜各种老爷的习俗。母亲蒸的大糕和圆馓首先是供这些活动用的。大糕放在堂屋长几桌上摞六七层高,像个小面塔,再插上些装饰,很好看。炸的圆馓有大有小,从大到小摞十几层,约三四十厘米高,放在面糕塔的两边,搭配起来很气派。这些供品用过之后就全都是我们和来串亲戚的孩子们的了。
母亲还会给我们蒸许多小面羊、小面鱼等,按照习俗,除夕晚上要放到米缸、面缸、水缸上面和门脑顶等处,初一过后才让我们吃,还要走亲戚送给堂表兄妹们吃。
母亲对我们是真正的好!她把全部心思和心血都无偿地投放到我们身上了!
母亲虽然遭遇不幸,早早地就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疼爱、抚养和教育我们子女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都烙在我们的心坎里。
母亲的恩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谨以这几段短短的回忆纪念我们永远怀念的亲爱的母亲!
梁二盛
2022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