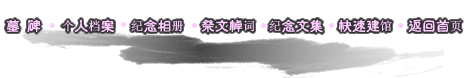清明节将至,思念恩师之情油然而生,虽然他已离我而去已七、八载了,每每想起,音容宛在……
60年代初,我读中学时,幸遇王同辰老师。那时,他教我们的图画课。记得,初学美术时,天真的我竟想一步登天,要求直接学“人的头部像”。王老师说:“好,那你每天先给我画10个圆交上吧。”说来简单做来难,无论怎么努力,我也不能把圆画规范。老师说:“要想画好曲线,就必须要先学会画好直线。”这时我才明白了,不管干什么事,都要循序渐进这个道理。
学水彩画时,我入了迷,便逃理科课去找王老师学画。见了老师后,他并没有批评我,只说:“我准备作画了,你来的正好,就给我配颜色吧。”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非但所配的色度不对,量也比要求多出了两倍。老师笑着说:“还是我来吧。”他很利索地在调色板上一合即成。我问其原因,他说:“因为我学过理化,为此能把握数量比例关系。”后来,他又指着一幅风景画,讲起了何为远景近景,何为消失点等绘画知识,我听了似懂非懂。老师见我一脸茫然,便解释说:“等你学了立体几何后,自然就明白了。”从此以后,我努力学习各科知识,再也不敢偏科了。
王老师经常领我们去写生,乡村的小桥流水,饱经霜的老人,校园里的花草树木……都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一个夏日里,他正在野外草地上全神贯注地写生。我见他汗流浃背,便偷偷地凑到近前去为他拭汗,不料,却弄翻了调色板,平日里老师作画总是一气呵成,我好心却做了错事,手足无措的不知如何是好。谁知老师看着身上“色彩斑斓”的我,仰天哈哈大笑后说:“真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呀!”当时我尚不明白,后来才渐渐悟到,老师的话语中包含着,对我们莫大的希望啊!
一年后,王老师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分别前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师徒二人通宵达旦,促脐长谈。临别时他引用《聊斋志异》中的一句话做为赠言:“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文革”中老师受挫,我也因父亲牵连而被遣返回乡,师生关系被迫中断。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老师,他赠于我的画笔及《人的头部画册》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粉碎“四人邦”后,我被分配到乡下教书。在90年代末,我赴县教委开会时去看望了老师。要不是我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身为县人大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的他,竟住在一个不足30平方米的小院里。他见到我很高兴,笑着说:“给我拿脑白金?高级,高级!你猜我当年求师学画时给先生送的是什么?一包花生,展开一看,里边还有土坷垃呢!哈哈……”他谈笑风生,依旧还是那么幽默。临别,他为我挥毫泼墨:“笔耕不辍”。
分手后,老师手扶着门框,目送我走出好远。可我万万也没有想到,此一别竟是永别……也许正是借了他的吉言,我后来才一步步走向了“笔耕生涯”。
(此文原载于2006年8月18日燕赵都市报资讯版)
周小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