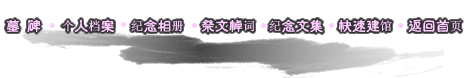火红青春
先父谢凤瑞,1922年(壬戌年)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一个大户人家,从小聪颖好学,梦想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那时战乱频仍,灾荒连绵,难以找到一张平静的书桌,他百辍不怠,还是成了西北大学地质系的一名大学生。当时已20多岁了,目睹国家的积贫积弱,他发奋学习,立志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
1948年毕业,不久西安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接管一些地质机构,他就参加了进来,1950至1951年在天成铁路工程地质调查队任工程师,活跃在天水、宝鸡、略阳一带的秦岭崇山峻岭中。当时交通条件极差,工具、行囊主要靠肩挑、手提、马驮,风餐露宿,还得携带枪支弹药应对土匪出没。艰苦的工作环境磨练了他坚强的意志,也激发了他的主人翁精神。1952年,当国家需要时,他依然离开了我们的妈妈-他的新婚妻子,远赴贺兰山主峰北段的小松山,参与新成立宁夏小松山队的铬铁矿找矿勘探任务。苦战三年,尽管期间大女儿出生,也仅过年回家探亲几天。
1955年下半年,突然接到西北地质局命令,让小松山队速迁青海柴达木。那时父亲已是技术负责,由他率领全队日夜兼程奔赴目的地,也顾不得去看一眼自己新出生的二女儿。原来,根据群众报矿并经初步调查,在后来被称做锡铁山的那一带发现了重要铅锌矿线索,急调小松山队就是要开展相关勘查工作。上级指示,在小松山队的基础上新组建锡铁山地质队,后来又叫西北地质局639队,任命谢凤瑞为总工程师。当时正值隆冬,在冰天雪地的大漠里冬季施工,做领导的父亲也不过33岁,带领着更年轻的一群人,以青春热血斗冰天雪地。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他们争分夺秒,奏响了一曲建设社会主义、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凯歌。到1958年12月,这群年青人就完成了锡铁山从预查到勘探的全部工作,胜利提交了“柴达木锡铁山铅锌矿床最终地质报告”。
1956年,我们的妈妈将两个女儿分别寄养到了亲戚家,也赶到了柴达木。妈妈名叫张瑞姑,1924年(甲子年)出生,河北定州人,50年代初毕业于兰州一个卫校。当时陇海铁路线天水-兰州段在建,她就在铁路部门的医院里做护士,与那时调查铁路沿线工程地质的父亲不期而遇,从此命运便与踏遍青山的地质郎联系在了一起。五十年代中期,青海尚没有通火车,从兰州去西宁的简易公路上尘土飞扬,汽车十分颠簸。由西宁向柴达木,更是要穿越大草原、茫茫戈壁与沙漠,必须带水、带吃的,夜晚在汽车旁搭帐篷过夜,野兽时常出没,往返一次就得十天半月。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她也投入到了开发柴达木的火热战斗中,在矿区为大家当起了医生。
1958年底,锡铁山勘探任务结束后,639队整建制调往祁连,与那里的地质队合并,新组建成了祁连山地质队(即青海地质二队前身),父亲仍然担任总工程师,母亲是队医。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祁连山队相继完成了香子沟硫铁矿、郭密寺多金属矿、小沙龙铁矿、玉石沟与拉硐等铬铁矿、红沟铜矿等众多勘探任务,为国家提交了大批矿产储量。直到1962年困难时期,国家下马了许多勘探项目,又决定恢复西北地质局(1958年西北各省成立了地质局),我们的父母才调回了陕西省。后来国家情况好转,1964年父亲被任命为西北地质局陕七队总工程师,领命解决金堆城钼矿开发中遇到的问题,母亲则在地质局医务所工作。
回到陕西地质部门时,父亲已经在秦岭、贺兰山转战了6年多,与母亲一起又在西北大漠、巍巍祁连工作了7年,他们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地矿事业,在那火红的年代里不负韶华,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
一家三地
我们家是个典型的地质之家,一家人离多聚少,除了过年团圆,全家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也没有几年。爸爸常年在野外,很少回来;妈妈后来也去了那里,离开了她心爱的孩子们。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父母双亲在青海柴达木、祁连山,大女儿寄养在位于陕西武功的西北农学院大姨家,二女儿和小儿子在北京姥姥家与二姨、四姨生活在一起。一个家庭,分居三地,相隔遥远,主要靠书信来往。那时可没有微信,电话也很少用,邮政鸿雁传书一次要很多天。亲人间深深的思念、盼望来信的焦虑,和相聚时的喜悦一起,都成了我们童年时光无法忘却的记忆!
不平常的生活可以造就不平常的情感与能力,这是平稳生活的孩子们难以获得的。我们清楚地记得,假期去探望父母,第一次看见西北一望无际的原野、涛涛奔流的黄河时的震撼,也不能忘记北京姊妹相聚时对绿树红墙、碧海白塔的眷恋。父母出差回来看望孩子,常带来大西北的土特产,每次都是让大家欢天喜地的。更重要是,长久别离的思念、相聚相拥的欢乐反而增加了姊妹间的亲情。没有父母的亲自照顾,孩子们都磨炼出了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培养起了学习的自觉性。以至于文革中父亲罹难,母亲被下放五七干校,未成年孩子们大的照顾小的、小的辅助大的,相依为命,竟然安全地度过了那段极其困难的岁月!
心系事业
在我们眼中,父亲严厉,母亲慈祥,二人是较为典型的严父慈母组合。尽管母亲去柴达木时二女儿不过一岁,儿子也是很小就放到了北京亲戚家寄养,可她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就乐此不疲地干家务,为孩子们做可口的饭菜,缝补、洗涮。爸爸就不一样了,无论何时,心思主要在工作上。
在爸爸去世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决定收集他的生平材料。因为他去世时我们都很小,对他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随着资料掌握的越来越多,爸爸工作的足迹渐渐清晰了起来。我们发现,孩子们出生时他虽然不在身边,可给孩子们起名总是和他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1952年至1955年,他在贺兰山寻找与超基性岩有关的矿产,给这期间出生的大女儿起名为“超”,不知是寓意超基性岩呢还是想超额完成任务?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初,父亲带领一帮年青人在柴达木的冰天雪地里对锡铁山矿进行预查,急切地希望它有巨大的矿石蕴藏量,于是那时诞生的二女儿在名字中就有了一个好听的“蕴”字。神奇的是,不知是上天的眷顾还是年青人孜孜追求的结果,锡铁山铅锌矿真以它的宏大与贡献被永远载入了矿业史册!
1958年,在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阵浮夸风,等父亲率西北地质局639队赶到祁连时,才知道人民日报上渲染的所谓大铜矿不过是一些铜矿化线索!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身为祁连山地质队的总工程师,我们的父亲承受了巨大压力,于是这期间出生的儿子就有了“铜”的名字。好在经过不懈努力,探明的红沟铜矿达到了中型规模,以富矿著称(平均铜品位3.7%),为繁荣地方经济做出了贡献。实际上,初步勘查的浪力克铜矿达到了大型规模,只是因为品位较低尚不能开发利用。但是,这期间探明的多金属、铁、铬、金等矿产,许多都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文革蒙冤
父亲家境殷实,为他读书、上大学带来了便利,可是后来被划定的地主成分也使他陷入了许多麻烦。尤其是他的几个兄弟在国民党军队供职,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又逃到了台湾,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他的头顶上始终笼罩着一团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旧中国,做为知识青年,父亲对国家破败、人民疾苦的情况深恶痛绝。西北大学读书时,他思想活跃,接触过一些进步人士。由于父亲离世突然,大女儿当时才十五岁,小儿子刚满八岁,大家对他早年经历的认识仅停留在一些只言片语上。可以肯定的是,在年青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时各种政治倾向的人都有,也不乏中间派、逍遥派,但他的人脉圈子是属于左翼的,其中的一些朋友直到解放后还经常往来。这次我们没有查到父亲加入共产党的时间,但知道当时他已经向组织说清楚了家庭出身、亲属去向等一些问题,也得到了信任与重用。
谁料想,WG中,造反派把这些又翻了出来,先是让父亲写交代材料,接着无休止的开会批判,逐步升级到批斗、游街示众,最后被彻底关押了起来,遭到审讯、拷打。家庭也受到了巨大冲击,两间住房被造反派抄家翻得底朝天,一些书籍、信件、笔记本等可疑东西都被没收了,爸爸在北京开会与中央领导的合影也被拿走了。妈妈、女儿、儿子都被强制在学习班里学习,让他们与爸爸划清界线;二女儿的名字被认为有资产阶级气息,被迫更改。一家人挣扎在绝望的边缘!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在京召开,囚禁中的爸爸从高音喇叭里得到了消息,曾盼望着国家能结束动乱走向正轨。然而,4月4日,也就是大会召开的第四天,他却被折磨致死,生命戛然而止在了47岁!我们曾经迷茫过,也愤怒过、憎恨过,但是想到那个动乱年代里连国家主席、老帅都不能幸免于难,是非曲直也就静待国家的公论了。
1978年,陕西省地质部门拨乱反正,为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干部、技术人员平反,父亲的沉冤终得昭雪!
千秋功业
我们的父亲在他47年短暂的生命里,为国家地矿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2008年青海省地矿局表彰建局五十周年十大找矿成果,锡铁山铅锌矿位列第四(《青海国土经略》2008年增刊,第21-22页),当时确认的矿床潜在价值为1815亿元,谢凤瑞被评为第一贡献人。今天,锡铁山铅锌矿为我国年采选规模最大的独立铅锌矿,声名显赫的西部矿业集团即由此起步,走向全国,走向了世界!
1964年至1966年谢凤瑞担任地质部西北地质局陕七队总工程师,领导了金堆城钼矿的补充开发工作,排除了氧化带以下难选冶矿石的存在,加上对矿体西、北边界、南部远景区的控制,新增可利用钼金属储量约一万两千吨,为金堆城钼矿后来的投产运营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980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地质系统评功授奖大会上,为金堆城钼矿开发做出贡献的单位被授予了“功勋地质队”称号。目前,金堆城钼矿钼生产经营规模居全球前三位,在国内同行中名列第一。
他工作经验丰富、专业技术理论功底深厚,离世前的三年多里在陕西省地质局地矿处任主任工程师,主管全省的矿产勘查工作。非常遗憾的是,却在年富力强时永远的走了!我们公开此文就是为了寄托哀思、激励后代、告慰英灵!
当代盛世正如父亲所愿,他的业绩早已开花结果、红遍大地! (地学君代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