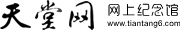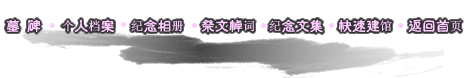保姆趁歇班,买好过年的肉,跑到我家来煮肉熏肉了。
大灶是父亲在世时,请人依照农村的大灶盘的,原来在院子里,后来在东厢房盘了一座,还镶上白磁砖,灶堂口有个铁门帘。农村人是真聪明,盘好的灶,根本不用风箱,全靠自然风,竟也混得风生水起。要知道,在电气化、天然气占领城乡的今天,农村大灶气宇轩昂、不卑不亢傲立一角,在机关也是一个特色景观。
母亲听说保姆来煮肉,站起来在窗前,看着忙忙碌碌的保姆,出出进进,我不知她在想什么。她拽着我,不断地指窗外,示意我看,我不明白她的意思。顺着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一堆捆扎好的干树枝,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墙根底下。我突然想起来,这些树枝,是父亲和母亲捡回来,晒干,剁成等长的段,然后扎好,堆放在那里的。于是问她,她忙不迭地点头,面色凝重起来,看着看着,她的眼里渐渐蓄满了泪,眉头紧皱着,嘴巴一咧,无声地哭了。
母亲想起父亲了。我忙引她到床前,给她打开手机,让她看抖音。
我何尝不难过?父亲走了三年多了,但是他种的韭菜、他捡拾的柴火还在,那整齐的木棍,每一根都依稀有父亲留下的指纹,残存着父亲劈柴的汗渍,那时的父亲过着是多么有劲啊!他一生不事稼穑、不进厨房,退休之后,突然改了脾气,母亲想种菜,他就把院子里的花砖掀开来;母亲想吃大锅蒸的包子,父亲就赶快请人砌大灶。居然还俯下身子捡树枝,这搁以前,连想都别想,用他的话说,他宁可闲在家里,也不去干“农村老娘们干的活”。
母亲蒸包子,七印锅,满满两屉,熟了后才给我们各家打电话,让去吃包子。那时候,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热气腾腾,父母的脸上,就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每到过年的时候,父亲累并快乐着,一趟一趟买东西,尤其是喜欢买猪肉,一扇一扇往家扛。父亲负责买,母亲负责在家做。年终时分,大多是三九四九,天寒地冻,母亲乐颠颠地剁肉,洗肉,然后就用那盘大灶,煮肉、熏肉。母亲做的熏肉,色泽红润油亮,香飘满巷,离老远就闻到那独特的香味,惹人馋涎欲滴。
母亲总是捡两块最好的熏肉给我,我女儿从小就吃着姥姥做的熏肉,胃口大开,以至当我定居深州后,她再也吃不到了。只是有一天早晨,对我说:咦,这个肉好吃。我一看,笑了,说:你嘴真刁,这是姥姥带给你的熏肉。
母亲终是想起什么,不断地往外走,总是想去看保姆煮肉熏肉,拦也拦不住,她就那么向窗外望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伤感起来,母亲脑梗后,失去了语言功能,神智并不十分清楚,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我从那年便再也没吃过母亲做的熏肉,想到此,不禁脱口而出:娘,以前你年年熏肉,年年给我两块,可是我再也吃不到你做的熏肉了。
娘一下子红了眼圈,哭起来了,我也哽咽了。我突然意识到,傻娘,依然是这世上最亲我的人,她为不能照顾我而难过,我依然是娘心中的宝。
父亲母亲捡拾的柴一年比一年少,不知道烧完以后,谁去拾柴。
但是,母亲做的熏肉,已深深印在我心里。风烛残年的母亲,是不可替代的爱,我好害怕,有一天,我会失去这唯一的最爱。
心里一紧,就紧紧握住了母亲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