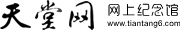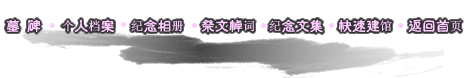九龙江的潮水退了又涨,母亲却永远停在了防坡堤上。我数着江面细碎的波光,每一片银鳞都映着她挑担跋涉的身影。
浒茂岛的晨雾还未散尽时,母亲便踩着露水出发。竹扁担压弯的弧度比月牙更锋利,左边是沾着盐花的带鱼,右边是浸透寒气的牡蛎。三里土路一脚深一脚浅,来到西良码头,排队上船,她总把船头最稳的位置留给海货,自己蜷依在船舷。石码渡口的青石板上,她脚印叠着脚印,把五个儿子的书包钱都踏进斑驳的纹路里。
那些年海风刻在她掌心的纹路,比渔网的经纬更细密。我们兄弟的碗里永远卧着海鲜,过年过节少不了鸡鸭,她却用筷子蘸酱油下饭。
楼仔埕承接了我们所有的童年。她教我们用咸草打草席、编饭袋的手艺,如今这些手艺再也见不到了。江水带走了太多故事,唯有她别在头上的头钗花,永远悬在记忆的枝头。
暮色漫过红树林时,我听见潮声在喊"位啊"。无数个清晨,她正是踏着这样的韵律走向市集,把整个九龙江的涛声都装进沉甸甸的担子里。现在五个儿子及其子孙站成防风林,终于懂得如何用她教会的坚韧,守护这片她深爱的咸腥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