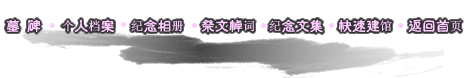父亲袁力先百年诞辰纪念
暨母亲魏景芳诞辰96周年
父親袁力先,原名袁履宣。祖籍四川省万源县,落居山东济南。
万源市,因地处万顷池和诸水源头,故名万源。是四川省下辖县级市,由达州市代管。位于四川东北部, 大巴山腹心地带,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和嘉陵江、汉江的分水岭。地处川、陕、渝三省(市)结合部,7个县市的交汇处。是连接川陕渝 经济、文化、交通的重镇,各路商贾云集之域,川东北边境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素有秦川锁钥之称。这里既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又享有“万宝之源”的美誉。万源历史悠久,夏商为梁州之域,周为雍州之地,秦属巴郡宕渠县。由汉到明,属达州通川郡东乡县。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年)割东乡县之太平里设置太平县,清道光时大略成现今之地域。民国三年(1914年)因与安徽省太平县重名,改名为万源县。1949年12月29日万源解放,隶属川北行署达州专区,1952年归属四川省达县专区,1993年7月由原万源县和白沙工农区合并建立万源市。父亲比喻万源的地势,“四边全是山,象口大锅,县城就在锅底。”
父亲1917年农历六月初三出生于万源县长石乡的‘陆家沟’,那是在地图上很难找的到,距离县城十几公里路的深山沟。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袁氏先祖于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马桑垭移民入川,迁徙至太平乡。谱记:世传九,长子九仁祖落居锅团圆(今长石乡),仲子九福祖落居北沙河猫耳坝,季子九成祖落居城口。经几代繁衍,后人分支,便有六户家族搬到这深山老林开荒种地,定居于此。父亲讲:因为这个大山沟里只有六户人家,便称为“陆家沟”。(又有人称为卢家沟,待考。)
祖父叫袁泰林,祖母叫李春发。祖父兄妹三人,姑奶奶嫁到外地刘家,称刘袁氏。幺爷叫袁泰高。奶奶的父亲是个木匠,祖父就跟着岳父学木匠手艺,由此来到县城谋生。
父亲是家中长子,弟弟袁建华比他小十岁,而小他二十岁的妹妹袁远华当他离家时还没有出生。因家境贫困,父亲幼年时曾经被寄养在亲戚家一段时间。前几年我们回家祭祖时,碰到一户人家,主人听说我们来自山东济南,就说他有个叔叔在济南,当年曾寄养在他家。原来是袁家至亲。后来问起幺姑,得到肯定答复。父亲不到十岁便上山背煤卖钱补贴家用。父亲曾说过:一次他独自背煤下山,在镇上换了个拳头大小的盐巴,在回家的山林路上,被一伙土匪抓住,搜身时他把盐巴藏在手心,土匪头子要拉父亲入伙给他当护兵,便挟持着往深山里走,幸好半路突下暴雨,天黑林密,电闪雷鸣,他藏在岩石后面,趁乱冒雨逃回家里,到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全身湿透,紧攥在手中的盐巴虽已化成指甲盖大小的一块,仍没舍得扔掉。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移到川北通、南、巴,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先后建立万源、红胜、城口三个县苏维埃政府。
1933年父亲在本县参加工农红军。父亲回忆道:将近十六岁的时候,被送到红四方面军在万源县城服务社的中药房当学徒,学习洗、切、烘、焙、抓的技艺,这就算是参加红军了。两个多月后,通江县红军服务总社负责人来检查工作,(红军根据地主要在通江县、南江县和巴中市,总服务社就是红军的后方机关。)被选中到总社去工作,社长和家里老人都同意了,就是老妈妈舍不得孩子走远了,经过做工作,妈妈最后也同意了,这样就随总社长来到通江县总社中药房。当时药房负责人是沈殿州,他对父亲很好。到了来年8、9月份的时候,敌人开始进攻红军苏区,形势日趋严峻,总社奉命向洪口场转移,后又转到了甘草坝,就在红军兵工厂所在地德仪城下。德仪城地形险峻,四面绝壁,只有四个口子可以上去,易守难攻,是红军造手榴弹、修枪炮、印钞票的大后方。随着反围剿斗争的失利,形势日趋紧张,到了10月份敌人占领了巴中南部。红军奉命准备向西转移,便动员年老体弱有病的回家,有亲戚的投亲戚,药房员工散去大半,好多小孩被家人领走,青壮年身体好的全部参加到战斗部队去,父亲年纪虽小,但坚决要求参军,被分配到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给团首长当了通信员,成为红九军一名战士。从此离别家乡父老,由“泥腿子”到枪杆子,转战南北。红九军由红十二师扩编而成,时任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
1934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在战争中发展,建立根据地,扩红招兵,规模达到顶峰,共辖第四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共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三个团,加上随行的党政机关、医院和工厂职工等,总计约十万人。1935年3月为策应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强度嘉陵江,开始长征。在这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年代,部队边走边打,恶战惨烈。那时团以下没有电台和电话,传达命令全靠通信员的两条腿!父亲讲:就象后来拍的战争电影一样,在过敌人封锁线时,把军帽用树棍挑出沟沿,吸引对方火力,敌人待换弹匣停顿的片刻,就连滚带爬的冲过路口。1935年红九军南下,在大川城与敌人发生激烈战斗,激战两天一夜,双方留下满山遍野的尸体,父亲夜里独自送信,月光下朦胧影着白惨惨的尸体,一不小心被绊倒就趴在了尸体上,可见战争之惨烈。父亲就是于大川城战役中入的党,介绍人是张林同志。
长征中,四方面军的部队来回三次翻雪山过草地,刀山火海,九死一生,走了不少冤枉路、经历了很多原来能够避免的苦难和艰险,吃草根树皮煮牛皮腰带更是家常便饭。父亲回忆说:有一次在过草地时,跟着团长带一营打前站,宿营在一栋藏式四层碉楼内。晚上七点多钟,整个部队已经休息,几个战士在楼下点火做饭,不慎失火,引起楼下弹药炸响,火势呼呼,火焰顺着木质的楼梯往上直窜,团长和营部住在最上层,被火焰堵住了楼梯口,只好把绑腿、背包带接起抓着窗户口往下跳,可惜绳索不够长,半空跌落下来,很多人不是摔死就是摔伤,父亲幸亏摔在一块较软的草地上,但还是摔晕过去,在担架上躺了好几天才醒过来。想想在那样艰难困苦的征途上,茫茫草地,饥寒交迫,战友们不离不弃,以疲惫虚弱之躯,轮流抬着担架坚持走出草地,那是什么样的情感和信念在支撑着呀!后来听说团长等好多战友都死于那场大火!当政委带二、三营赶到时,看到一片惨状,无不放声痛哭!此事惊动了军委,并下达死命令:各部队宿营一律不得住进碉楼。
红四方面军南下打到四川边境天全芦山一带,红军伤亡很大,没有打出去。而后又退到甘芦地区休整,等二方面军会师北上,第二次进草地。部队到芦河时调父亲给团政委当警卫员。不久政委调总部学习,父亲到总部保卫部学习,后编到总部警卫营。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二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8月部队到达陕南的天水铺,这时政委学习结束,带着父亲回到部队。第二天在天水铺与胡宗南部队硬碰硬打上了,这一伏打得很惨烈,消灭敌人一个师多,我方也伤亡严重,当时团长政委都牺牲了。激战中,父亲和警卫员一前一后站在政委身旁,是在一个半山坡上,突然敌人一串机枪子弹横扫过来,前面的警卫员因站位靠下,被击中头部,居中的政委被击中胸部,两人当场牺牲!政委身后的父亲位置靠上,子弹从左腿膝盖弯部穿进,又从右腿钻出,当时就昏迷过去,经简单包扎后由担架转移,一路颠簸,到陕北的瓦窑铺一方面军医院,已经是一周之后了,两腿伤口化脓生蛆,肿胀如桶!由于没有麻药和消炎药,只能采取原始方法,由四个强壮的卫生员按住,医生用筷子缠上盐水纱布条,从伤口这个眼捅进去从另一个眼穿出,然后拉锯似的来回抽拽,血水浓汁喷流而出,父亲疼的大汗淋漓,几次痛晕过去,其经历常人难以想象!幸好子弹没有伤到神经和骨头,没有落下特别严重的伤残。此后父亲走路都有些瘸拐,但他从来没有申请过伤残,每提及此事,父亲说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四方面军五个军加上总直属队总人数约为42764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遵照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指挥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六个师十六个团约二点二万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父亲伤愈归队后仍给新任团政委当通信员。当时政委在总部学习,结业后,两人一路急行军追赶部队,结果还是晚到了一天,黄河渡口已被敌人封锁,归队不成,父亲分配到红军总部特务团第三营九连当战士,后当班长,驻防在延安南的富县。不久国共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给干部战士们换上了国民党的军服。思想上不通,说什么也不愿穿。经过上级反复教育,下命令同志们才穿上。这时父亲曾给老家写过两封信,没有回音,未找到家。
1937年2、3月份,一路浴血奋战的西路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最终失败,父亲的老部队红九军全军覆没,6500名红军将士殊死搏斗,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1937年12月,组织选拔他到通信学校第十一期学习无线电报收发报,也通学了无线通信原理、电台结构、操作维修、英语和电码等,在红军队伍里当时可以说是最高科学技术部门之一了,对于一个没上过一天学的父亲来说,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也曾打过退堂鼓。那时候父亲长得短小精干,在一次运动会上赛跑,个子最小却跑的最快,冲过终点线时,老校长欢喜的把他抱着举起来。当知道父亲想回前线时,老校长亲自动员做工作,甚至下了死命令。 “睡觉以前躺在床上,闭眼用手指在肚皮上默画一天学的东西”我们小时候他经常教我们的学习方法,正是他当年刻苦学习的经验和体会。经过加倍努力,总算留下学成。1938年6月,父亲被分配到延安清凉山的红军总部电台五十四分队电台实习,不久便开始正式值班,很快又当上了台长。
抗日战争开始后,1938年12月,父亲和另一位十期学员带着两部大功率电台“挺进敌后”,随彭真同志从陕北到晋察冀边区,组建中共北方局电台分队,并任队长。彭真对电台通信非常关心,经常指导工作,问寒问暖,关怀备至。有次父亲收到战士捎来的一件毛领棉大衣,从口袋里发现一张“彭真同志收”的纸条,才知道是上级发给彭真同志的,他又转送给了经常值夜班的父亲。电台分队隶属于中共北方局机关,归地方编制,如果长期干就得脱军装,父亲多次直接找上级电台中队长钟夫翔同志(曾任邮电部副部长)提出要回部队上前线,彭真同志也亲自找他谈话,希望能继续留在北方局工作。最终父亲于1939年2月调到黄永胜为司令员,王平任政委,詹才芳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的二团任电台队长,后又调任六分区九团、三十四团。从1945年12月起,又调到冀东军区(詹才芳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委)的十五分区任电台区队长,后到十二分区任通信股长。在唐山以北,承德以南的“冀东”山区与日本鬼子和伪军周旋打游击,参加了“百团大战”。当地比较有名的地方一是 “三屯营”,二是“喜峰口”。“三屯营”传说是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训练精兵的总部大营。“喜峰口”则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隘。八路军正是在当年前辈抵御外侮的丛山峻岭之间,与侵略者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殊死搏斗。电台是部队的命根子,失去电台就像个聋子瞎子,无法判断敌情,不知道自己和友军的位置,不能及时接受上级指令,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这样的处境就相当可怕。因此电台分队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待遇也比战斗部队略高一些。当时只有团级干部才有马骑,电台分队从连、营级就配备马匹了,行军时起码要配备一个排的警卫,路上父亲他们在马上打盹休息,一到驻地,部队宿营休息,他们则马上要忙碌地架设天线、调整电台信号、及时联系上级,然后是昼夜值班,保证随时能收到并传达上级命令。部队转移时,他们又要收电台、撤天线、整理文件,最后才能撤离,再去追赶部队。有一次夜间转移,他们不小心竟然扎到敌人营地里,幸亏发现的早,急忙悄悄的退出来转进大山里,与团部连续三天失去联系,把团长差点急疯了!父亲说:那时候他们行军除了军用装备外,随身必备着一茶缸用猪油炒的辣椒和一捆子烟叶,电台值班熬夜,常常是好几天连轴转,实在困了就抽烟吃辣椒来刺激神经和提神,有时就连树叶子、干草都拿来搓巴搓巴卷起来当烟抽,长年累月如此,就落下了哮喘和胃炎等慢性疾病,以致后来长年不敢吃辣椒和韭菜了。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担任冀东军区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1948年11月部队进驻唐山市,任唐山警备司令部通信科长。1949年4月,奉华北军区命令整编,冀东各地方部队升格编入主力部队。以唐山警备1团为基础与14分区独立14团合编为628团;以秦皇岛警备团(原13分区警备团)为基础与12分区独立2团合编为629团;以14分区独立13团为基础与唐山警备2团合编为630团;以冀东军区机关及其直属队编成华北军区独立步兵第210师机关及直属队。1949年8月编入20兵团67军序列,改番号为陆军第201师,父亲均为该师通信科长。该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其主要任务就是在山海关、昌黎、滦县一带破袭、阻击华北蒋军傅作义部向东支援东北,其后又配合东野围歼天津之敌。
1950年 6月部队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1师,作为第三批部队入朝参战,开赴前线。父亲调任67军通信科副科长,军司令部通信科长。先后参加了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等战斗和战役。志愿军武器落后,地形不熟,面对敌人排山倒海的火力覆盖和漫山遍野集群坦克的冲击,我67军将士以血肉之躯,逐山逐水苦斗恶博,所有预备队甚至连军部直属机关、警卫连、通信连、炊事员、卫生员等都拿起武器上了战场!战争期间,代军长李湘不幸病故,这是志愿军逝于朝鲜战场的最高将领。
1952年12月父亲奉调回国,进入河北张家口总参通信兵学院指挥系学习,离开了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1956年8月毕业,调任68军通信兵部主任(部队正规化后各军通信科长改成通信兵主任)、通信处处长。68军其前身是华北军区第六纵队,1949年2月,六纵队在北平奶子房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8军,隶属于第20兵团。文年生任军长,向仲华任政治委员。1951年6月部队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军长陈坊仁,政委李呈瑞。1954年9月奉命回国,划归济南军区,驻防江苏徐州及其附近地区(代号0978部队、6063部队)。1960年至1969年10月张鋕秀任军长。1975年部队移防吉林省吉林市。1989年撤编。
1964年父亲又调任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全家也跟着进了省会大城市,那时候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家具,象床、桌椅、橱子等都是公家的,搬家时把被子褥子衣服等装进战时用过的“马褡子”里,就可以动身了。父亲在武装部的几年,主要是深入厂矿检查指导民兵建设和负责征兵工作。“文革”期间参加并完成了“三支两军”“大联合”的任务。
1969年底,由于形势混乱,为了保障国家的正常通信和战备,中央决定全国邮电部门拆分,邮政部门划归省交通厅管理,电信业务部门划归军队管理,设立山东省电信局,为省军区直属的师级单位,机关就设在原省邮电局院内。局长、党委副书记为原省邮电局的老局长聂鑫同志(中央红军出身的老干部),原昌潍军分区政委韩华同志任党委书记、政委,父亲调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同时很多军队干部被调入各个电信部门。父亲在省电信局的工作主要是主管生产建设和正常的通信业务,在战备通信工程建设中,为局里争取到大块基建用地,保证了很多重大工程项目的圆满完成。
1973年底邮电部门合并,成立了山东省邮电管理局。军队干部撤出该系统,父亲又调任济南市警备区副司令员。济南警备区由原市武装部改编,承担了整个济南地区军分区的职能,不仅负责民兵的组织建设和训练、征兵、退伍安置等工作,同时还下辖几个步兵团,担负守卫周边的桥梁、仓库、机关要地的任务。对地方上还要参加省市组织的抗洪抢险工作。父亲曾挂名市抗洪抢险指挥部副总指挥,虽恭填末位,却每年涝季都要直接指挥民兵到黄河大坝上巡逻和抢险。
1979年,父亲改任济南警备区顾问组长(正师职)。1980年离职休养,1985年10月定为副军职待遇。离休后先后入住济南军区第三、第一干休所。在所内积极参加干休所组织关爱下一代的“讲信仰、讲党史、讲军史”等宣教活动。
父亲1955年被评为中校军衔(正团级),1961年晋升为上校军衔(准师,行政11级)。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朝鲜三级“红旗勋章”、军委所授二级等。
2004年12月28日,戎马一生、慈祥宽厚的父亲离开我们,享年88岁。
母亲魏景芳。1921年3月26日生,老家在河北省遵化县西铺镇接官庭村。遵化县地处冀东重镇唐山北部,是清朝时期关里关外的交通要道,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清东陵就建在该县的西部,这是一个饱受中国封建传统礼教的古老县,“遵化者,遵从教化也”,好像还是康熙皇帝起的名字。“接官庭”这个村以前是朝廷来东陵祭祖时守陵官员在县界的接待站。
姥爷叫魏国全,姥姥叫李淑芝。相传魏家祖先是由河北邯郸地区魏县迁徙到遵化县,姥姥的娘家在河北省宽城县杏儿峪村,也是算个大户人家,后来又迁徙至冀东的迁西县。太姥爷家在当地开了个骆驼店,家境还算富裕。听舅舅们说:当时那里是关里关外过往车马、骆驼等商队的集散地,人来车往的络绎不绝,其繁华景象可想而知。太姥爷家是当时村里首屈一指的富户。姥爷在魏家排行老三,兄弟三人分家后,分的家财不多,又不善经营生产,加上前面连续三个女儿,种地没有劳力,只好雇用几个短工,家道中落,全靠姥姥上下打理、里外维持。母亲的性格随姥姥,倔强泼辣,敢作敢当。北方女孩稍大些便要缠脚,母亲不愿意,大人给缠了自己就偷偷解开,折腾了三番五次,最后还是当抗日游击队长的大舅爷(作战牺牲,革命烈士)来家看到后,说要打倒封建主义,三下五除二把裹脚布给撕扯下来了。从此魏家女孩们都不裹脚了。再大些母亲又闹着去上学,上了几年小学。在敌后抗日风起云涌的形势下,母亲识文断字有文化,干起了村妇女主任。八路军开办建国学院,母亲报名入学就读财经系,正式加入革命队伍。当时同在冀东军区十二分区司令部的侦查股长李惠民,与父亲相处的很好(父亲是通信股长)。他是二姥爷家的“二姐夫”,便将母亲介绍给父亲,从此冀东结缘,情系川冀,热土亲情,叶茂根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随部队内线外线连续作战,母亲则带着孩子随留守处四处转移打游击。多少年后,我们去看望年迈的大舅时,他说:那些年,不管大姐的部队转移到哪里,什么马兰峪、三屯营、喜峰口、燕河营。。。。他都能找到,然后回家报个平安信。
母亲曾任67军速成学校学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冀东军区、210师、67军等部队司令部收发室收发员。1955年转业至唐山市花纱布公司任营业部经理。1956年父亲到68军任职,当时是全家六口分居四地,母亲为了照顾父亲更好的工作和全家团圆,于1958年办理了病退随军手续。到徐州68军后,曾参加组建军机关家属服务社等工作。为了革命事业和我们这个大家庭,母亲默默奉献,无怨无悔,终身操劳,积劳成疾,于1986年5月27日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们的父亲和母亲是极忠厚善良的人,一生经历无数风波曲折,始终忠诚守纪,克已奉公,淡薄名利,正直俭朴,宽容大度,从不整人,他们的优秀品质和高尚道德,是我们终生享用的精神财富。
今年是父亲百年诞辰、母亲九十六周年诞辰,特集相册并撰文记叙以为永久纪念。此举完成了我们多年的心愿,上可告慰在天英魂,下可激励后代子孙,善莫大焉!
伟大的父亲母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袁晓龙 袁晓国 袁冀川 袁冀山 袁冀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