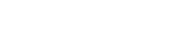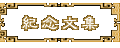
周道如砥,坦然可观 ——追念黄颂杰先生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应奇教授 2020/3/10 10:01:00 浏览:344
年前就听说黄颂杰先生因重症住院,让人心里蒙上一层不祥之影,但是当我一早从李蜀人兄的状态中得知黄先生于今晨仙逝的消息,心情还是沉重而悲痛。
说起来,黄先生还是我的“座师”:1993年春夏之交,我从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硕士毕业,我的导师范明生先生请颂杰先生来主持我的论文答辩。我们那时候的学制是两年半,范老师那一届其实有两位学生毕业,其中有一位已经按时答辩,而我是为了与博士生入学衔接而特意推迟毕业的,所以黄先生那次是“特意”为我一个人而赶到淮海中路622弄7号来的。还有点儿特殊的是,那一年我其实写了两篇硕士论文,前一篇写新儒学,范老师“临时起意”不予通过,我也只好“临时起意”赶写了一篇简论从德国观念论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其匆促粗糙自然不言而喻,但黄先生还是高抬贵手让我通过了,年深日久,只记得他似乎说:看得出来文章写得很急,但还是有些“火花”,而且你敢于下论断!
虽然如上述黄先生是我“座师”,但我一直与他并无交往,一个原因当然是我从硕士毕业就离开上海了。本来范老师是希望把我留在哲学所,再在职在沪上念一博士学位,但后来因为留所的事不了了之,其他的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第二次亲承黄先生教诲,已是很多年之后,应该是在杭州的一个会议上,一堆人正在聊天时,黄先生特意走过来对我说:你编的那套“实践哲学译丛”不错,我也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得到来自前辈的肯定和鼓励,我自然是受宠若惊,而且感激莫名。的确,黄先生不但在考虑那些问题,例如他在广州的这个演讲;而且是我的“同道”:我记得他至少编了两套书,一套是哈佛哲学教材系列,另一套是当代哲学家研究系列,都是享誉哲坛,让人受益无尽的。
印象中是在那次聊天后,黄先生特别告诉我,他在主编学报英文版,希望我有英文论文的话可以交给他。面对如此盛情邀约,我只有支支吾吾的份儿了,我不好意思告诉他:自己虽然翻译了几本二三流的书,主编了几套一二流的译丛,但我的英文是我的所有“功课”中最糟糕的。
我到上海后参加过一次中西哲学与文化年会,似乎那次黄先生也作为前辈参加了,他看到我露出很亲切的表情,也许我那时刚到沪上“惊魂未定”,竟也未能与他好好地谈一谈,只是有个感觉:黄先生有些老了,但他那机敏通达干练的精气神尚在举手投足间在在呈现。有一次我和郁振华兄偶然聊起黄先生,我们都认为,在他所置身的那个风起云涌波谲云诡的学术“共同体”中,黄先生乃是中流砥柱式的让人心安的存在。
去年五六月间,我的一位过去的学生到杭州某校求职,在各项条件都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因为稍有些个人性的因素而受制,我偶然了解到用人部门主持工作的一位领导曾是黄先生的博士生,由于事出紧急,我在从沪返舟的大巴上微信给孙向晨教授,问来了黄先生的联系方式,就直接在车上给黄先生电话,想请他代为澄清一些情况,帮我为这位学生尽最后的努力,黄先生闻听我这非分之请不但未推脱,而是热情地答应了下来,而且黄先生那时正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此事后来虽然仍未成功,但是黄先生替我做的那种“担当”已经大大超出我所能言谢的范围,事后想来,简直对我构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巨大压力——我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太鲁莽了?太强人所难了?难道我就没有或者说竟至于以堂皇的正义感来包藏对自己学生的一念之私?无论如何,能够“宽慰”我自己的,我觉得黄先生应该是不但不会以此为意,而且是能够理解我的所作所为的。
去年底,我偶然看到黄先生的一份自传,他在其中详述自己的家世生平,娓娓而道,让人读来颇有兴味。尤其其中提到1957年的高考,让我联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是那一年高中毕业参加大考。这份偶然的巧合似乎让我平添了一份与黄先生的亲近感。而回想起来,大概也正是颂杰先生身上那谦谦君子和霭然长者的风范让我作为一个其实平素与其并无交往的晚辈和后学,“敢于”在他面前提出从常人和世俗礼仪看是“无礼”到有些“过分”的要求的吧!
黄颂杰先生千古!
2020.3.9,正午,阴雨中于千岛新城寓所
- 暂无评论!
- 发表评论文章评论(共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