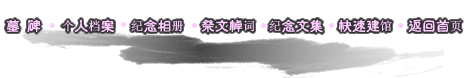一身正气的共产党人
——深切怀念中共黑龙江省委原常委、中共黑河地委书记王钊
刘佩勋
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曾任中共黑龙江省省委常委、中共黑河地委书记王钊同志,于2016年9月7日在哈尔滨市逝世,至今快两年了。我经常回忆和深切缅怀这位让我永生难忘、值得尊敬和学习的老领导。
王钊同志原任中共伊春市委书记,1963年5月调黑河,任中共黑河地委书记。组织决定,让我做他的秘书。两年后,我又被调到地委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由于工作性质决定,我仍然不离王钊书记身边,经常跟随他一起活动,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
我在王钊同志身边前后工作了三年多。在他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有益知识和经验;同时也亲身体验到王钊同志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老干部、老领导的高风亮节。至今铭刻在心,时刻怀念着与王钊同志身边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他是我心中最敬佩的老领导,最亲密的良师益友坚守信仰,对党忠诚。我读过王钊同志于2011年所著《八十个春秋》一书,了解王钊
同志16岁(1939年),在抗日战争炮火纷飞的年代,在家乡山东农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回忆:“在我们家西屋的小油灯下,举行了入党仪式,区委组织委员庄严宣布:举起你的右手宣誓吧!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名正式党员啦(当时入党没有预备期)。”王钊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曾这样写道:
党,我亲爱的母亲,
人类的光明、希望、智慧和力量,
你终于来到了我的身旁。
在一个普通的夜晚。
星星格外晶莹,月亮也格外明亮。
我站在党旗面前,
高举右手宣誓: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从此,刚满16岁的我,
正如一个雏儿,
开始在慈祥的母亲怀中成长……”
王钊同志1963年来到黑河就赶上“七一”,庆祝党的生日,又写了一首诗:
《敬礼!我的母亲》“……
党,亲爱的党,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跟着您前进的脚步,
走过光荣的历程。
……”
王钊同志走过的这三十多年,从基层到县、市、省,都是担任地方领导或部门领导,一贯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要干就一定干好,干出成绩。
王钊同志到黑河后也是这样,始终是心里装着全区100多万人民群众,团结和带领地委“一班人”,为改变黑河落后面貌绘制发展蓝图,日以继夜,兢兢业业勤奋工作。
王钊同志不怕苦,不怕累,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着我和许多同志。对王钊同志来说,没有节日,没有假日,起早贪黑,拚命工作。同志们这样形容王钊同志:“好像他心中有一团火总在燃烧,不知疲倦,不知休息,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王钊同志每天工作到深夜。我跟随王钊同志接连参加三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经常是白天紧张工作,晚间开会写材料,有时通宵达旦。平时还要挤时间读书学习。
我清清楚楚记得,“文革”第二年夏天,我们地委直属机关干部和当时被打倒看管的“三反份子”,一起从黑河坐着能装几百人的大船,去大五家子农场支援麦收。船上有的人在聊天,有的人说说笑笑,有的人在观看或欣赏黑龙江两岸风光。我发现只有一个人坐在甲板上聚精会神地低头看书。这个人就是当时黑河地区最大的“走资派”王钊。我靠近他的身边,发现原来他正在读《毛泽东选集》。
有人小声说“王钊真行!他都当了“黑鬼”蹲在“牛棚”里,出来放风要马上下船干活了,还这么认真学习看书,真是好样的!”
由于王钊同志工作成绩突出,1966年初和当时的省委秘书长陈俊生同志同时被任命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正当王钊同志满腔热忱,拚命地为黑河人民贡献自己力量的时候,“文革”爆发了。王钊同志被迫害多年,经得起政治风云的考验,刚被“解放”就被省委选中,调任中共大兴安岭地委书记。
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树典型 抓根本
王钊同志1963年来黑河,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首先,深入到黑河地区所辖的爱辉、北安、德都、孙吴、逊克、呼玛、嘉荫七个县,了解和掌握基本情况。然后,有选择地进一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很快发现和解决了两个突出问题:
一是,农业生产经营比较粗放,单产很低,南两县(北安、德都)亩产不足二百斤;北五县(爱辉、孙吴、呼玛、逊克、嘉荫)亩产不足百斤,不施肥或少施肥,广种薄收,虽然有着广阔的耕地,粮食却不能自给。
王钊同志和地委“一班人”针对不同的情况,对南北县实行不同的政策。要求南两县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为主,北五县以改变粗放经营,提高单产和开荒扩大耕种面积并重,提出“北二(亩产二百斤)南到三(亩产三百斤)产量翻一番,人植百棵树,一亩保收田”。王钊等领导同志不仅提出了明确的农业发展目标,而且注重调查研究,抓住典型,大力推广。
爱辉县四嘉子公社四嘉子大队和小三家子大队,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季里,截河劈岭,修了一条二十四华里的渠道,使河水穿过洼地爬上高山,引入平坦的原野,开辟了新的稻田区,创造了北五县有史以来新的创业范例。
王钊同志抓住这个典型,以地委名义号召全区人民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开展学习四嘉子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运动。这一号召得到全区广大农民热烈响应,对于改变农业生产粗放经营方式,提高粮食产量,实现北五县粮食自给有余,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是,从内地调入黑河的一部分干部不安心工作,只看到黑河天寒地冻、边远偏辟、经济基础差的落后一面,对黑河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发展前途广阔、边境重地的光明一面,看的却不够,所以,总想调离黑河。
为此,有针对性加强了干部思想教育,开展了热爱边疆、建设黑河的思想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广大干部为祖国开发边疆是最光荣事业的责任感。
同时,王钊同志还写了“北陲寄语”的长篇文章,撰写了“黑河是个好地方”歌词,让歌舞团的同志谱曲,并广泛组织群众传唱,鼓励大家热爱黑河,热爱边疆。
以身作则 亲自动手
王钊同志对于会议上的讲话,大都是自己亲自起草,不用秘书或其他同志代劳。他写完了征求我和有关同志的意见,让我们帮助修改。王钊同志即席讲话从来没有稿子,都是让我或其他同志记录,需要下发的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成文。
对于工作总结、有关专题报告材料、工作研究等文章,王钊同志都是把大家集到一起,他出思想(谈自己的想法),出题目,大家议论,拟提纲,然后每人分一部分起草。王钊同志也分个题目,同大家在一起,坐在会议室同一张大桌子上写作。最后,让我把大家写的内容“串”起来,王钊同志亲自审阅修改后成稿。王钊同志对于自己的文艺作品也是如此。他每写一篇散文、诗歌,都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定稿。
亲自指导办好《黑河日报》
王钊同志对中共黑河地委机关报——《黑河日报》,非常重视和关心。他亲自指导办报,通过报纸来推动全区工作。他来到黑河不久,就多次向地委组织部领导提出:“报社党员编辑太少,不适应党报需要,要尽快从地直机关或各县,选调几名有一定基层工作经验与政策、文字水平、适合做新闻工作的科级党员干部,来编辑部工作。”随后,就从地直机关和外县调来六、七名干部,一下子使多年名额不足的编辑部得到了充实。
王钊同志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报社的领导力量。他亲自从地直部局院长中,为《黑河日报》社挑选了专署二办(文教办)主任郭洪亮同志,任黑河日报总编辑,使报社的领导班子得到了加强。
1991年,曾任黑河日报总编辑的杜广州同志,在黑龙江《新闻史料》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回忆王钊书记的文章,题目是:《王钊同志与黑河日报》,其中谈到了王钊同志如何指导办报的具体情节:
“王钊同志身为地委书记,百事繁忙,却对新闻工作仍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可能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记者有关吧),他经常亲自跑到编辑部来“吹风”,或是传达上头精神,提示报道思想。或是就当前工作中心,某一事件,某个典型,提出他的报道思路。毫不夸张地说,在他任职三、四年期间,《黑河日报》的一些重要报道,没有一件没得到他的指导的。
他不但给地、县级领导定写稿任务,并且自己动手,带头给报纸撰写社论、评论、杂谈、诗歌、散文等各种体裁的稿件,每年不少于20几篇。”
“……他也来到编辑部,建议我们宣传这个典型,把“四嘉子精神”推向全区。我们报道组写了“新愚公劈山引水”的长篇通讯,送给地委审阅,一份份送回的大样,唯独王钊同志的大样改的最多,最认真。样边上的白纸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有他对文字结构的建议,也有一段段精辟的议论。他不满意原定标题,亲自试拟了几个后,让我们再斟酌,精心提炼一下 。
当时,地委正在召开有各县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结束的那天,王钊同志突然宣布增加一项内容,对我们撰写的长篇通讯,要求大家帮助修改或选上好标题。与会同志七嘴八舌,列出几个题目,最后由王钊同志为这篇通讯确定了“劈山引水创新天”的标题。同时,他亲自指派宣传部长张连俊为通讯配写社论,又让他爱人潘青同志与我们一起研究,把报道进一步精雕细琢后,才在报纸上发表。”
“1966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王钊同志又到编辑部,建议我们开辟专栏,组织地、县、乡三级干部写文章,学习焦裕禄,宣传焦裕禄,推动干部作风转变。他自己身体力行,在两个月间,就为《黑河日报》撰写“学习焦裕禄札记”十五、六篇之多。”
酷爱文学 作品丰硕
王钊同志非常喜爱文学创作。每天无论工作多么紧张多么繁忙,都要坚持读书、学习和写日记。首先是学习政治理论书籍,同时也十分喜欢阅读文艺书籍。他既读书,又坚持写作。
王钊同志的爱人潘青是专业作家,他俩真可谓是“琴瑟和弦、珠联壁合”,经常一起探讨文学创作的题材和构思。潘青曾经写过许多以林业为主题的小说和剧本。
王钊同志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而且很多作品和他的工作经历有关,大多是颂扬林区工人和黑土地上的劳动人民,也有一些是感悟人生哲理的散文、杂记、诗歌等。有的作品还被收集到《中国散文精华一一关外卷》。
他对黑龙江的山山水水,特别是他工作过、熟悉的地方,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的许多作品被结集出版了《王钊文集》(分为三卷:纵横谈、散文卷、诗歌卷)。出版后,颇受读者喜爱。
关心群众疾苦,慷慨解囊
1964年冬天,我跟随王钊同志搞“社教”,到爱辉县幸福公社长发屯大队,住在一户贫下中农家。男主人有病不能下地干活。女主人叫刘桂芳,也有严重的眼病,视物模糊。
王钊同志问她:“治疗过没有?”
她说:“我家里生活这么困难,治不起就挺着吧!”
王钊同志当即就掏出钱来,让她立即去黑河医院检查治疗。刘桂芳说什么也不收。
王钊同志说:“就算我借给你的”,这才勉强收下。
“文革”时,她听说王钊同志被打倒,专程到黑河看望王钊同志,并还钱,王钊同志不但没收,因为她眼病未痊愈,加之她丈夫还有病,生活仍很困难。
王钊同志和其爱人潘青同志又给了她不少钱。刘桂芳流着眼泪说:“我永远忘不了你们的恩情!
也是在这个屯子,有一天,一位女社员(名字记不清了),是广州人,找王钊同志“告状”。她说她原住广州,解放军四野解放广州时,遇有一位连长姓徐,她嫁给他不久,就跟着这位连长复员,回到家乡黑河爱辉县北三家子村。后来生了个孩子,由于婆媳关系不和,离婚后离开村子,嫁到现在这个村子。好几年了,她说几次去看孩子,孩子父亲和爷爷奶奶都不让见。她哭着说:“我非常想见孩子,常梦见孩子”,她曾去过几次都不让见,找过村干部也未能说服徐家的人。
说来也巧,我曾跟随王钊同志去过北三家子村,见过她说的原丈夫徐连长。王钊同志安慰她,并立即亲笔给北三家子社教队长和村干部写了封信,让他们帮助她见孩子。
事后,这位广州女人,顺利地见到了多年未见到的亲生儿子。她非常感谢王书记。她说:“要不是王书记写信,不可能见到亲生儿子。”
体贴下属,讲革命情谊
王钊同志非常关心和体贴下属,很讲革命情谊。我给王钊同志当秘书,头一次去省开会,住在哈市107(和平邨宾馆)。
有一天晚上,王钊同志让我抄写一篇文字较长的内部资料,并说明天早上必须奉还。不多一会,他又来到我住的房间,端了一杯酸牛奶说:“今晚你会熬夜的,饿了就喝这杯酸奶吧!”
同屋,合江地委书记的秘书、牡丹江地委书记的秘书,都对我羡慕地说:“你的领导王书记多么好哇!”后来我才知道,宾馆每天睡前,专供给来开会的各地委书记,每人一杯宾馆做的酸奶。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喝酸奶,不知道酸牛奶是什么滋味。喝着王书记送来的这杯酸奶,我深受感动。
王钊同志经常给《黑河日报》写社论、评论员文章,及其他文艺作品,所得稿费从来不留下自用,完全送给同志们。从1964年到1966年,地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团办公室的许多办公用品,都是王钊同志用他稿费购置的。就连夜餐费也是由王钊同志的稿费中支付的。地委机关的体育用品,有的也是根据王钊同志的意见,用他的稿费购买的。
更使我永生难忘的事情:1965年2月24日早晨,我母亲突患脑溢血被送到医院,当天夜里即病故。
翌日早晨,正在我母遗体入殓的时候,总团办公室张振鹏同志对我说:“你看谁来了?”
我回头一看,是王钊书记和地委副书记、专员丁逢水、地委副书记胡绍中,来为我母亲吊唁送行。
我含着眼泪说:“感谢三位老领导!”更没想到的是,当天下午,我在家接待来看我的同志们 时,王钊同志又在当时社教总团副团长、专署副专员张庆生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我家,安慰我说:“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你要经得住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幸(指前几天离婚,今日老母突然离世),你不要太难过,要坚强起来,好好睡觉,好好吃饭,保重身体,带好孩子……”我不禁热泪盈眶,更深深体会到党组织对一个党员的关怀,体会到党的温暖。
在“文革”后期,我的大女儿刘英,考入加格达奇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读书。一个星期天,时任大兴安岭地委书记的王钊同志和爱人潘青,到学校看望她。我女儿给我来信说:“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感动,纷纷称赞王书记是一位讲革命情谊的好领导。”
尊敬老红军 耐心教育“老黄”
1964年夏天,王钊同志正在主持地委常委会议,就听走廊里有人吵吵嚷嚷。原来是当时黑河市直唯一一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老黄”同志,非要见王书记不可。王书记立即对大家说:“会议暂停,我去接待这位老黄同志。”人们都知道“老黄”同志没读过书,没有文化,经过干部文化学校扫盲班学习,才会写自己的名字黄希崇。
地委安排他为黑河专署办公室副主任,工资待遇行政15级。离休后在家闲呆,本应很知足。可是总有人在背后唆使他上访“告状”,要求增加工资。
王钊同志耐心听他“诉苦”,和他说了一个多小时我在旁边听王钊同志说:“老黄同志啊,你是老革命,对党有贡献,大家对你很尊重。可是你经常到地委专署大院吵吵嚷嚷,影响大家工作,你说这样好吗?有意见可向组织反映,不应该到机关这样吵吵闹闹。组织上给你的待遇并不低,你应该知足。你要保持光荣,像个老党员,给大家做个榜样。如你身体还好,应该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王钊同志的谈话语重心长,对“老黄”同志真起作用。过后,王钊同志亲自和专署党支部书记、专署办公室主任刘玉岐说:“你们应当耐心帮助老黄同志,让他过党的组织生活,大家不要歧视他,在生活上多关心和照顾他……”
严于律已 清正廉洁
王钊同志一贯严于律已,清正廉洁,从不搞特殊化。
在黑河“社教运动”期间,社教总团办公室都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同志,我们单独成立了党支部,我被选为党支部书记。有时过“党日”,因为看到王钊同志工作太繁忙太劳累,就没有通知他。王钊同志当时因为这事,曾严厉批评了我。他说:“我是党员,必须按时过党的组织生活,不要因为我是地委书记工作忙就可以特殊。在我们党内没有特殊党员,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原则问题,是个党性问题”
我随王钊同志到各县,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下乡蹲点,从来都是轻車简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记得1963年,我跟随王钊同志第一次去北安市,市委接待我们,午餐比较丰盛,领导成员都参加作陪。王钊同志说:“再不要搞这么多菜,你们也不要作陪了,就我和佩勋,两个人就按规定四菜一汤吧。”
王钊同志生活十分俭朴,从不讲吃讲穿。
王钊同志一生,最后是在黑龙江省政协主席的岗位上工作了8年离休。政协的同志们对他的评价:“王钊同志不管到哪里,都是带着一颗红心,满腔热忱而来,又带着满身正气,两袖清风而去。”
王钊同志调任省政协主席后,一位同志曾在“人品、文品、诗品--王钊文集评析”一书中写过一段话:“他为人民奉献了一切,唯独没有为自己谋取点什么。就说他的四个子女,除了受到他这个“走资派”父亲的株连、倍受白眼、贬斥、压抑之苦外,没有因为他这个革命领导干部的父亲而受到格外关照。他们靠自己的勤勉和奋斗,上大学、成才、入党、提干,每个人都同父亲一样,保持着一种平民化的品格。”
王钊同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壮丽的一生。
今天,我们缅怀王钊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守信仰、对党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品德和风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听党的话,跟党走,做个好党员,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