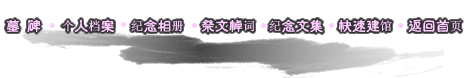瑰丽人生
——深切怀念潘青同志
刘佩勋
时如流水。转瞬间,潘青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
我和黑河的许多老同志一样,每当回忆起和潘青同志接触或共事的情景时,都深感痛惜!
潘青同志是一位优秀作家。她学识广博,才情横溢。写作是她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她把全身心献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从而赢得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许和尊重。
潘青同志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她对事业热情,对生活热情,对他人热情。
“真没想到她是部长、作家”
1963年,潘青同志随爱人、中共黑河地委书记王钊同志来黑河。组织上考虑她写作方便,曾任命她为中共黑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她总是以饱满的热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努力创作。
记得,那是1963年冬天,我跟随王钊书记,在当时的爱辉县爱辉公社西三家子和北三家子两个大队,参加“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住在一位姓李的老乡家。
有一天中午,我们刚端起饭碗,潘青同志突然来了。我们让她吃饭。她看我们吃的是大碴子粥,高兴地说:“我就是喜欢吃大碴子粥,大葱蘸大酱 !”
我跟她开玩笑说:“你在省城哈尔滨,什么好吃的都有,怎么爱吃这农村的饭菜?”
她说:“你不知道,我在家里也做过大碴子粥,可说啥也做不出这个味道来!”
王钊书记先吃完饭,就到大队办公室去了。我和潘青同志一边吃一边唠,我问她:“你是有事,来找王书记的吧 !”
她说:“没事,我也是来下乡的,老王知道我要来。”
她接着说了一段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她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如果不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总是游离于生活表层,像油一样地漂浮在水面上,与沸腾的生活格格不入,浮光掠影,没有生活的深刻感受和体验,是不可能写出真正像样东西来的;只有深入群众,甘当小学生、才能吸取智慧和营养,激发创作灵感,增强创作实力,才能写出反映生活、热情讴歌人民群众、具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倾向的作品来。"
住在老乡家里,潘青同志不仅和我们一起工作,参加会议、走访、讨论材料、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早晚还要帮助女主人搞些家务劳动。她和女主人睡在一个炕上,天不亮就和女主人一同起来做饭。帮助女主人喂猪、喂鸡、洗衣服、看小孩,什么活都干。
女主人很年轻,孩子小,刚会说话,特别闹人,有时哭起来没完没了。年轻的妈妈实在没招,就动手打孩子,这时潘青同志就把孩子抢过来抱在怀里。
女主人说潘青同志很会哄孩子。潘青同志刚来时,我只告诉这家男主人和女主人,说潘青同志是王书记的爱人。他们并不知道潘青同志的身份。
过了几天,我们熟了,我告诉他们潘青同志是部长,是作家。他们很惊讶,异口同声地说:“真没想到她是部长、作家!”
特别是女主人深有感慨地说:“潘部长穿戴那么朴素,一点架子都没有,唠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的嗑,对我们家一点不嫌弃,哈活都帮我干,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女领导干部……”
潘青同志因省文联要开会,提前离开西三家子大队,要走的头天晚上,躺在坑上和女主人唠个没完。半夜孩子可烧得很厉害咳嗽得厉害,一摸身上发烧,潘青同志急忙起来,帮助找医生、打针、吃药。
第二天早晨女主人跟我说:“我这小崽子可气人了,有点病更闹人,昨晚折腾半宿,给他灌的药都吐出来了,说什么也不喝,最后还是潘部长哄着他,把药灌进肚子里 !”
潘青后志走时,女主人和邻居的妇女,都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来送她,大家都亲切地说:"潘部长别忘了我们,你一定再来啊!"
“她太辛苦了……”
1964年春天,潘青同志为黑河评剧团参加全省调演,编创了一出评剧,叫《小春江畔》。因时间紧,任务重 (同时还要完成另一部作品),不得不昼夜突击。
她拟出这个戏的框架后,写一场,排一场,她一直跟导演和演员在一起。在排练中,潘青同志观看,发现问题不断修改剧本。大约有二十天的时间,每天白天忙一整天,晚上还得加班到深夜。因为当时剧团每天晚上有正常演出,所以只好等到晚9、10点钟,观众走了,才开始排练《小春江畔》。
记得,那时地委正在组建黑河地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总团领导机构,准备开展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王钊书记工作非常繁忙,既要抓点上的社教运动,又要抓面上的生产、工作,我跟随王钊书记经常工作到深夜。
有一天晚间,我们开会研究修改材料,快到12点了,王钊书记说:“散会吧!”
可是,王钊书记并没有回家,他说:“我还要到评剧团接老潘呢!”
王钊书记让我回家睡觉。然而,我这个当秘书的,怎能让领导同志深更半夜一个人去剧团呢? 于是,我就跟王钊同志徒步到了剧团。
进剧场一看,潘青同志正在舞台上和大家“说戏”呢! 剧团的同志们跟我说:“我们熬夜习惯了,每天睡早觉,白天休息,可是,潘部长怎么受得了?晚上大家讨论完了,她白天还要修改剧本,不然,晚上没法排练啊!潘部长太累了,太辛苦了!”
回家的路上,王钊书记手持电筒为潘青同志和我照亮,我看到潘青同志十分疲惫的身躯,深深被潘青同志这种为了事业废寝忘食、勤奋工作的精神所感动。
“我永远忘不了她的恩情……”
在1964年的冬季,我有幸随同王钊书记参与“社教”活动,前往当时的爱辉县幸福公社长发屯大队。在那里,我们寄宿在一位贫下中农的家中。家中的男主人因病无法从事田间劳作。女主人名叫刘桂芳,她同样患有眼疾(睫毛倒生),导致视力模糊。
她出身很苦,从小给人家做“童养媳”,丈夫有病故去,她又嫁给现在这个丈夫。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由于我们在她家住过,王书记让她去黑河街里时到家里坐坐。这样,她便认识了潘青同志。
不久,刘桂芳丈夫病情加重,治病需要一笔费用。刘桂芳在村中借不到钱,实在是“走投无路”了,硬着头皮来到王钊书记家求援。王钊书记不在家,刘桂芳就如实地和潘青同志说了。潘青同志劝刘桂芳不要“上火”,便拿出一笔钱 (具体数我记不清了), 给刘桂芳。
当时,刘桂芳流着热泪说:“潘部长,我感谢您,等治好了我丈夫的病,一定把这些钱还给您!”潘青同志说:“别说还了,快拿回去给你丈夫治病吧!"
1967年“文革”当中,刘桂芳听说王钊书记被打倒看管,潘青同志在哈尔滨,专程来黑河看看王书记家,然后到了我家。从刘桂芳的嘴里,我才知道上述情况。刘桂芳说:“潘部长真是好人哪! 我永远忘不了她对我的恩情啊……”
事隔多年,不知刘桂芳现在何处? 如果她知道潘青同志逝世的话,一定会更加悲痛的。
X X X
1994年,国庆节前夕,我和老伴赵惠玲,从大连回黑河,路过哈尔滨。老伴提议去探望王钊书记和潘青同志。不巧,王钊书记为省政协去云南“招商引资”。
我们从潘青同志憔悴的脸上看出,她的病是不轻的。但是,她还像以往那样热情、乐观,谈笑风生。
老伴说:“潘部长、我和佩勋在大连大女儿刘英家住了几个月,有一天刘英下班,给我们带回一张哈尔滨出版的《生活报》,上面有记者专访:《王钊家事》一文,读后感到非常亲切,佩勋当即就给王书记和您写了一封信,不知接到没有?"
潘青同志指着桌子上的信说:“早就接到了,不知道你们去大连,大连可是个好地方啊!”
我们问起潘青同志的病情。她说:"我是多病缠身,每天吃好几种药、特别是每天晚上不吃药不能入睡。有时,我的确被疾病折磨得难以忍受。但是,我始然没有被疾病压倒,我想活着就得和疾病做斗争!"
她告诉我们,她每天坚持看书、看报,有时还写点东西。
唠了一会,她领我们看了她家楼上楼下几个房间,并说有的间壁不太合理。我们怕她说话多了,身体受不了,几次站起身来要走,可是她再三挽留。
最后走时,潘青同志送我们到门外,拉着我老伴的手说:“你也有病,要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这里的技术水平,还是比黑河高的。如果要看病,我让我女儿耀红 (哈医大二院党委书记) 协助称 !”
潘青同志病到过般地步,仍然在关心着别人,怎能不使我们感动 !这是我们和潘青同志最后一次见面,真没想到竟成永诀 !
潘青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兴安苍苍,
黑水茫茫。
潘青同志,
千吉流芳!
1998年8月15日于黑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