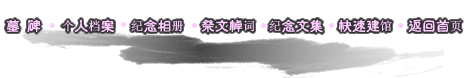写给妈妈的话
王跃红
妈妈:当你的生命之火即将燃尽的最后一刻,你默默地忍受着病痛的煎熬,在病房里度过了一个个寂静而漫长的黑夜。
岁月似流水,点点滴滴地流入了你生命的长河。
也许此刻你的思绪又飞回到那寒冷、残酷的解放初期,你忘不了作为“东大”的学生参加土改工作队的情景……;
也许你又听到了朝鲜战场上那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你曾怀着腹中蠕动的小生命,奔赴朝鲜战场……
或许你的思路又飞回到那郁郁葱葱的大森林,在那里,你曾忘我地挖掘着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胸中激荡着毫无倦怠的创作激情;
也许你又在同你笔下的人物交谈,那些被你誉为“林海雄鹰”的林区工人和干部们,还有那位从柴达木盆地骑着骆驼走来的戴红头巾的姑娘……,那些从你文学札记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在依依向你道别;
而你最心爱的小女儿好像又在向你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她的奇闻轶事…… 然而,生活远去了,生命的鼓角在渐渐地平息。你只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真不愿意给你们添麻烦……”便沉沉地睡去,再没有醒来。
为了生命的价值,你曾义无反顾地付出过代价,然而生命的回归对于你却淡淡地没有丝毫的奢华,你不无遗憾地走完了人生的终点,妈妈,你好像有话没有说?
那一刻,我眼前的你,仿佛像冰河一样凝固了,生命的韵律变得苍白、无声。然而记忆好比大自然一样不能消逝,人的精神和心迹最终将达到永恒。
“要自强、自立、俭朴地生活”
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你和爸爸总是对我们说:一个人要自强、自立、俭朴的生活。
三年困难时期,你经常自己动手,把旧衣服翻新。为我们缝制与众不同的新衣,又把穿破的毛衣、袜子补了又补,你告诉我们“笑破不笑补”。你从不要求特殊待遇,把每月供给的烟、酒票证,都送给需要的同志们;生活中的你最喜欢穿的是那双黑布鞋,最乐意吃的是自己家小园子里亲手栽种的蔬菜和果树上的水果。
1961年,伊春市发生了历史上特大的洪水,山洪爆发,伊春城迅速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在抗洪救灾中,爸爸被钉子扎破了脚,感染红肿着,他仍然指挥着各级干部日夜奋战在抗洪第一线上,顾不上回家。
这时候,我们兄妹四人中有三个得了伤寒病,高烧不退,哥哥最重。小学的同学中不断传来因“肠穿孔”而死亡的消息,但是,妈妈你没有丝毫的抱怨和悲观情绪,你忙着把一批批逃难的群众让进家中,楼道里住满了妇女和孩子,你热心地照顾安慰大家,送上吃的、穿的、用的……
那一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来到伊春林区视察,王光美还亲临我们家,她要亲自了解一下市委书记的生活状况。她打开锅盖,看到的是玉米面大饼子和“糊涂粥”,室内的家具只是简单的木桌和几把木凳,生活再简单不过了。
可是,作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又是作家的你,已把全部热饮都投入到火热的林区建设中去了。你多次深入到林场工人、干部中间,足迹踏遍了大、小兴安岭,你深深地被那雄浑的木工号子所感染,为“冬运大会战”的热潮所振奋,写下了著名的长诗《长歌大青山》和《木把人》、《老翠哥》等小说、散文。
不到30岁的你,就完成了电影《万木春》的创作。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一觉醒来看到的你,总是不知疲劳地挥笔疾书,直到凌晨三四点钟,你的台灯还一直亮着。如果因为生活琐事占去了你宝贵的时间,你会变得焦燥不安,一旦投入写作或外出采访,你马上会精神畅然。
听不到你抱怨辛苦,也看不到你表白功绩,看到的是那一本本的采访笔记,那里记下了工人、干部们典型的人物和方言俚语,从而形成了你文学作品中凝炼的语言和各类人物中迥然不同的个性。勤奋的生活积累,酿就了你诗歌、散文中奔放的激情。充满生命力的小说语言,正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尽管在“文革”期间,你的文学创作被迫中断,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你重新踏上了大戈壁的采风之旅,深入藏民之中进行考察。你从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带回了关于南国林业发展的宝贵信息,即使腿脚不便,你也坚持前往沿海经济区,观察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前往中苏边境,了解边贸的演变;你还随作家代表团东渡日本,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即便在住院期间,你也不放过任何机会,采访身边的女医生、女教授……你如饥似渴地积累素材,提炼生活,迫不及待地想要弥补十年动乱中错过的时光。
直到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更加日以继夜,再度修改你的长篇小说《苍山如海》,你说电影厂正计划拍片。这期间,你和爸爸还携手出版了《大荒纵横》和《黑土情怀》两部书,字里行间、情浓意切,你们纵情讴歌着大森林的美丽,和那些忘我地奋战在林区的工人、干部们。
你曾以爸爸为原型,刻画了一位新上任的市委书记,为妥善安排知青大返城而历尽艰辛的历史一页……,在你丰富的内心世界里,充满了对人民群众的热爱。用你勤奋的笔耕和卓越的艺术灵感,记录下了改天换地的时代新风,却唯独没有注意你自己的身体。
在你患病期间,我深知你最大的心愿,是修改完你的长篇小说《苍山如海》,我便安慰你说:“也许,我和爸爸能帮你修改一下?”
你若有所思地摇摇头说:“我已经修改三遍了,只是有的细节要非常真实地体现出来,比如山洪冲散了像山一样高的原木垛,甚至有人牺牲了,要表现如此壮烈的场面,非要有生活体验才行啊!”你正是这样,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着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完美统一。
“要多学本领,多见世面”
记得我们刚刚懂事,你就常对我们说:“要多学本领,多见世面”。
尽管你日夜繁忙地工作、写书,但你总是不失时机,为我们创造学习的机会,虽然当时家里的生活费用并不富裕,你还是鼓励哥哥参加国防体育俱乐部的活动,省下钱,来买电子原件和木模,让他学习安装收音机和制造航空模型;你和爸爸还把毛主席诗词和古诗,写好了贴在门上,让我们比赛背诵,并经常教我们练习书法。
你们经常买来许多革命故事书籍,像《红岩》、《小英雄雨来》、《奥斯特洛夫斯基传》等中、外名著,教育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这些对我们后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都带来深刻的影响。
1966年,当“十年动乱”的狂风恶浪袭来的时候,我们四个子女中大哥不过15岁,最小的妹妹耀琳才8岁,那时你在哈市从事专业创作,我们随爸爸住在黑河。正当“炮打司令部”的前夜,形势紧张得一触即发;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这场“运动”的意义所在,全国已开始了“大串联”。你特地打来了长途电话告诉我们:走出去,锻炼自己,见见世面”。
不久,我们真的被选上进京代本致北京,去见毛主席了。可是,当我们重返黑河的时候,想不到一夜之间,我们的生活一下子颠倒过来,我们骤然从“大队长”,“地委书记的子女”变成了”黑五类子女“。
在学校里,我们被督促着当着父亲的面,在斗争会上宣读着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是非的“批判稿”。家被抄了,书柜全被贴上了封条,所有能查到的钱,都被没收了,就连房盖上、门把手上,也被“革命的标语口号”占领了。从这时起,我们才对“经风雨、见世面”,“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有所感悟。
不久,爸爸被频繁地批斗,眼睛和腰也受了重伤,很快被“隔离审查”。从此,我们身边没有了父母,也没有了经济来源,一直照顾我们生活的姜姨,也被迫离开了我们。
那一年黑河的冬天格外的冷,在零下40℃的天气里,8岁的妹妹耀琳常被不懂事的孩子们推推搡搡,散了小辫,掉了鞋子,脸上冻起了大血泡,懂事的耀琳从不哭闹,学习总是最好的。不久,我也得上了“营养不良性贫血”。
无依无靠的我们曾给你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但均无回音,我们多么盼望得到妈妈的关心呀。20多年后,你告诉我说,当你听说了这一切,心急如焚,无奈你当时被打成“黑作家”,作品被当成“大毒草”批判,已是身不由己。
可是,我们真的有了母子相见的机会却又如此之难。
有一天,我从同学那儿得知你被从哈尔滨揪到黑河来“批判”了。开斗争会这天,我偷偷地顶着熟人的白眼,跑到文化宫的一个角落里,当我看到你被推到挂满大标语的舞台上,陪爸爸挨批斗的情景,我的心缩成了一团,尽管太远,看不清你的脸,但是知道你还“健在”的满足感,足已使我忘掉了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接下去,我便快步跑回家,告诉弟弟、妹妹“妈妈真的来黑河了”……
多少年以后往事重提,我问你:“造反派难为了你吗?”
你只淡淡一笑说:“还都是些学生”。
但我知道,你是一位自尊自强的女性,你视尊严如同生命,但经过多年革命斗争的磨炼,使你本来刚强的乘性,此刻更能忍辱负重。
斗争会一结束,你不得不带着妹妹耀琳,赶回哈尔滨继续接受“批判”。等待你的却是患了直肠癌的姥姥,已病重卧床,三天没吃东西了。守寡半世的姥姥,终于经受不住精神的压抑和癌痛的折磨,辞世而去。你匆匆为姥姥办了后事,便又去接受“审查”。
耀琳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了。每当你们“黑帮队”开饭的时候,耀琳只能站在你们的队伍必经的路旁,远远地看上一眼队伍里的妈妈,但什么话也不能说。
苦涩的生活,磨炼了耀琳顽强的毅力,她不仅成了海城小学校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还读遍了“省文联图书馆”里的藏书,后来干脆找来《辞海》看起来。这为她以后的记者生涯,奠定了丰厚的文学基础,更筑造了她自强不息的人格魅力。
1968年初冬,爸爸被监管进了监狱,几个月后,我们才知道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消息。我和哥哥只能带着小弟弟到偏远的山村插队去。此时你又被下放到清河“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我们一家六口人分在六个地方,但我们每次接到你的来信都不亚于一次“精神会餐”,你总是鼓励我们不要怕困难,要向革命前辈学习,积极要求进步。
几年中,我们几个先后入了党,哥哥连年被乡亲们推荐上大学,终因“家庭问题”而被搁浅。而你自己原来就患有肾盂肾炎病,白天干着推小车,运红砖的重体力活,晚上还要写稿子到深夜,但是为了孩子们,你仍然拖着疲惫的身体,为我们织了漂亮的毛衣,缝了棉背心,又托人买来半新的大衣邮集给我们。
看到这些充满母爱的衣物和信件,我们倍觉温馨,因为我们必竟有两年多没回家了。每当春节到来时,知青们都返城回家过年去了,可对我们来说,“家”的概念,只是一间空的小屋和一把很大的黑铁锁。唯有看着你那充满文学色彩的来信,使我们在逆境中有了精神寄托。
1978年,爸爸调回省里工作,“家”也在哈市安顿下来。耀琳丛哈中毕业,决定放弃留城的机会,而去大兴安岭林区锻炼自己。当时,父母身边只有她一个子女,但是爸爸、妈妈欣然同意了他的选择,让她到大森林里去积累生活素材,锻炼意志、品质。
耀琳不负众望,她成了山里仅有的一名女电锯手,在一次锯原木时,小姆指被锯掉一截,她却满不在乎。她还成了林场一名坚持原则的检尺员,一时被运木材的司机们传为佳话。
两年后,恢复了高考,耀琳一边劳动,一边自学,以文科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大连外语学院法语系,并连续四年被评为大连市、校的三好学生。
一场浩劫终于结束了,经历过这场风风雨雨,我们变得成熟了许多,我们更懂得了工农感情的珍贵,更理解了实事求是办事的真谛。特别是妈妈你那外柔内刚、含蓄坚韧的个性,和勇于吃苦耐劳的精神内涵,直到后来的一次经历中,使我更加深了对你的了解。
1974年的秋天,作为医大学生的我,随医疗队来到牡丹江林口县刁翎公社。走在乡村的小道上,几位乡亲和我拉起了家常,一位年长的老乡,仔细地端祥我说:“咋好像见过你,真像土改那咱儿的潘淑清(母亲的原名)。”我惊讶地说:“那就是我妈呀!”
这一戏剧性的插曲,我马上写信告诉了你,你很快给我写了一封足有十几页长的回信,讲述了3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往事:你说人生真像戏剧,想不到30年前工作过的地方,30年后女儿又来到这里。
你告诉我,那一年你只有18岁,为了投奔革命队伍,你偷偷地离开了姥姥,随东北大学的土改工作队,开进了这个叫作“土匪窝”的小山村。由于受到日本鬼子的压,榨和土匪“胡子”的掠夺,村里的乡亲们十冬腊月天没有衣服穿,只能用“洋灰袋子”遮住身体,工作队一进村,乡亲们都躲在地窝棚里,把糊窗纸舔个小洞儿往外看。
当时,环境非常残酷,工作队里的一位年轻的队长,就是在寒冬腊月的一个深夜里,被土匪光着膀子,拉上山,砍了头。我曾问过你,“怕吗?”
你笑着说:“当时只知道干革命,搞宣传,还演出《白毛女》中的赵二嫂,向乡亲们宣传共产党领导穷人闹翻身的道理……”
后来,这些生活素材都编进了你的小说、戏剧中。如果说当年你是热血沸腾,投身革命,但到了1951年,抗美援朝的战火燃烧在鸭绿江边,刚刚结婚的你,又带着身孕,自愿参加了“祖国慰问团”,奔赴了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每天顶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强忍着饥饿和困倦,你走一路,编一路,有的队员病了不能出场,你就串场为战士们唱上一首家乡小调。
后来,队伍打散了,你又跟着战士们打过了三·八线,当你回国时,已怀孕八个多月了……然而对于这一切,你都视为“应该干的”,从不炫耀,可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却是很难做到的。
你一生都在追求理想,你那勇于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坚定性,来自于你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难圆的中秋月
妈妈:如果说你所投身的革命事业,和你所倾注一生的文艺创作道路,是你生命之所在,是你甘愿荣辱自取的话,那么你心爱的女儿耀琳的牺牲,却是对你刚强的意志品质的又一次考验。
耀琳,她毕竟是我们家庭的骄傲,她聪明好学,勤奋宽容,博采众议,超凡脱俗。她那压抑寂寞的童年,使父母更关注她的成长;她那火一般的热情,使朋友们印象难忘;她乐观开朗的性格,使孩子们一接触她,就会异常兴奋,她洒脱锐利的笔锋,使她的文章深深地吸引着它的读者。
只要一有空闲,她会随手涂几张漫画在电视节目中播放,一旦她走进家门,便会妙语连珠,歌声不断,所以家里人都乐意和她共进晚餐,因为她那富有感染力的表达,能报人地把天南地北:海内外的趣闻轶事都介绍一遍。
作为《新晚报》的首批记者,耀琳开始了十年的新闻采访历程。他主编政法界的稿件走法场,访民警,查大案,诉民情。在她的笔下,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人民卫士:郭铁军、杨光、安东……,还有那些犯罪思悔的大学生。妈妈,你总是最忠实的读者和评论家。
正当耀琳在新闻界,连续被评为“优秀党员”,做报社党委委员,正待培养提拔之际,外交部发来了通知,要借调耀琳夫妇赶非洲使馆工作四年。
去,还是留? 体弱多病的妈妈,你又一次支持了耀琳的选择,你太了解女儿了,她还年轻,30岁出头,正是增加阅历的时候。毕竟是远走非洲了,你们真的恋恋不舍。
而耀琳呢,一件浅蓝色的牛仔棉外套,一头齐耳根的短发,亲亲可爱的小儿子,再和妈妈摆摆手,一甩头发便离开了家……出去闯闯,长长见识,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远的诀别。
1992年8月28日这天上午,耀琳去非洲8个多月了,中秋节临近,你思念女儿心切,便翻出耀琳的影集看起来,一种不祥之兆似乎在说:“走得太久了,好像看不见她了”。你慢慢地走进园子,看着小虎头在踢球,正当你帮助捡球的时候,突然跌倒了,手腕骨摔伤。
两天后,特地从外地赶回家来的爸爸,带来了噩耗,外交部正式通知家里,耀琳已于8月28日上午10点左右,在大西洋溺海身亡。
天知道,人世间真的会有“感应”存在吗?真是晴天霹雳,这对于六七十岁的父母来说,精神几乎被摧垮了,爸爸终于抑制不住巨大的悲痛,失声痛哭,他连声说:“太可惜了!”
几天来,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园子里来回地踱步。妈妈你刚强地坐在那里,强忍着不让泪水滴下来,因为我知道,你会像以往在逆境中那样,为爸爸分担痛苦,可是十年动乱的创伤才刚刚愈合,一把刀子又戳在你的心口上。这时候,大哥耀中正在俄罗斯拍摄《东方大河-黑龙江》的电视片,我问你:“是不是想让耀中回来吗?”
你摇摇头说:“耀中为拍这部片子,筹集资金多么难! 还是让他安心把片子拍摄完成吧。”几个月之后,哥哥完成了任务,才知道家中所发生的一切。
就在耀琳去世的第三天,按到了罐琳发自非洲的最后封信。我们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这封格外沉重的信送给了你,读着亡人的来信,那字字句问都撕扯着你那早已破碎的心。
耀琳用那活泼的语言在信中说:她非常喜欢大西洋的海水。她去了闻各世界的非洲大市场和水上村庄,并写了文章邮给晚报;她说实在太想念“小虎头”了,让他画一张画邮来……她说爸妈照顾“小虎头”太辛苦了,她要给家里买台直角平面的电视机……一位多么可爱、孝敬的女儿,一位才华横溢,有着旺盛生命力的青年人,她才只有34岁。
为了寄托哀思,也为耀琳那仅有5岁的儿子留下母亲的纪念,全家人和报社的领导、朋友们300多人,冒着连绵的秋雨,将耀琳的骨灰安放在墓地。爸爸妈妈满怀对爱女的深情,共同写下了墓志铭刻在了石碑上。妈妈还特意选了一张耀琳的照片,作成烤瓷像,镶在墓碑上。
几十年的疾风苦雨,从没有摧垮你们的意志,人生呵,好比一个磨盘,就是血、是火,总要碾过去。你把巨大的悲痛强压在心头,从不见你在人前掉过一次泪。为了纪念耀琳短暂而充实的一生,你决定把耀琳生前发表过的,和待发表的四十多万字的文稿编成书。爸爸亲笔为书题名为《耀琳采风集》,你亲自为书作了序,你把对女儿的千般思、万般爱凝于笔端。
在序的结尾,你无限深情地写道:“耀琳的一生,是一支美的童话,又是一支最现实的凯歌......她走了,从太平洋的一侧飞向大西洋,她在大西洋的彼岸做了短期的停留,有不无遗憾地继续往前方走去......但愿她一路平安!“这本书印刷出版以后,你和爸爸就把大部分书赠送给了公安战士们,另一部分献给中小学的老师们,做为一本珍贵的的学习英雄的教材。
然而女儿那精灵般的音容笑貌怎能挥之而去?静下来的时候,你总是凝神地望着耀琳那笑盈盈的照片,在它的旁边,插上一束淡粉色的玫瑰,你精心地把耀琳那三十多本奖励证书,收藏在小柜子里,似乎某一天,女儿会再次走进家门。
一次偶然的发现,我们看到了你,在1993年1月留给耀琳的儿子“小虎头”的一封信和小礼物,你在信中写到:“虎头:这是妈妈给你的留念,一块剪纸,一条彩球手帕,一个气球,一张她的奖状。这四件东西多么赋于联想:美丽的童年,彩色的生活,作人的品德,永远奋进不息的追求。保存它吧! 终生保存,永不忘记,你有一个最可敬爱的妈妈! 姥姥”
就在耀琳牺牲后的第一个端午节,我刚下班回家,便接到了你的电话,你问我:“还有粽子吗?”
我脱口而出“有”,你说:“如果屈原能吃到粽子的话,耀琳也许会的……”。
我马上回答说:“你放心,我这就送去”。
我立即冒雨出门,买了粽子,直奔松花江快步走去。风夹着雨,越下越大,望着昔日耀琳常在此游泳、散心的涛涛江水,此时,却如悲怆不断的泪水倾泻在江面上,激起千万层波澜。我奋力地把一个个粽子远远地投向江水中,心中默默地为耀琳祝愿……
从此以后,家里少了多少歌声和趣闻。妈妈你过度思念女儿,糖尿病也日益见重。你曾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多少次跌倒了,你又顽强地站起来,几次肝昏迷醒来,你又盼望着转机,总盼着能恢复体力,重新拿起笔。直到严重的胸水、腹水使你持续几个月,只能半坐位入睡,那浮肿的双腿,起了水泡,难以行走,你却不愿麻烦别人,自己坚强地扶着墙,一步步地移动,而很少诉说痛苦,周围的人无不赞叹你的涵养和坚强。
我知道你一生中最喜欢种花,,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给你插上满瓶的梅花、梨花,又换上丁香花。
夏天里,那两支怒放的黄玫瑰,曾给你带来多少欢欣,我总想把春天和夏日,送进你走不出的病房,可是到了秋天,中秋的月亮又要圆了的时候,你却终于没能回到你那一直盼望回到的“家”。
你静静地走了,没有嘱咐和要求,更没有表白和留言,然而你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位有着高尚情操的女作家;你那不朽的精神和深沉的母爱将与我们同在。
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