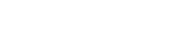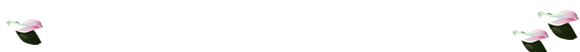“左联”旗帜下
华蓥星光 2016/5/3 21:08:00 浏览:839
我们今天纪念“左联”,就是要学习“左联”盟员不怕困难,不畏艰险,自居亭子间而心怀天下的风范,学习他们始终与党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为实现党的目标、任务不遗余力,不惜为之献身的精神。
一屠光绍
1930年12月,张泽厚从成都出狱后回到岳池县顺梁寨老家。在家里凑足路费后,立即动身去上海。他到上海时己近新年年关。这以后陆续见到了一些老熟人:原在成都西南大学任教时的同事杨邨人、原上海艺术大学的同学程少怀都来向他转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的活动情况,动员他参加“左联”。程少怀还告诉他,他们在上海艺大的老师朱镜我、李初黎、冯乃超、潘梓年、郑伯奇、李铁生、沈起予、沈学诚都是“左联”成员。在他们的介绍下,张泽厚也于1931年1月初加入了”左联”,并担任”左联”组织部干事,在组织部部长钱杏邨(阿英,1900-1977,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领导下投身左翼文化运动。
张泽厚加入“左联”没几天就发生了“左联”五作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秘密杀害的事件。李伟森(李求实)、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五位“左联”作家于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捕,2月7日在龙华被枪杀。后来调查的证据表明,五烈士被杀,与他们的“左联”作家身份无关,他们也不是在参加“左联”活动时被捕的。他们是中共党内斗争的牺性品。(详见朱正:《一个人的呐喊》)“左联”五烈士是在参加“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会议时,被人告密让特务和巡捕房抓走的。而告密者竟然是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康生,他为了帮王明消灭党内反对派,不惜用借刀杀人的手法出卖党内同志,直接导致23位党的重要干部被国民党杀害,其中包括左联五烈士。(详见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著:《康生传》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五烈士被杀并没有吓倒张泽厚。他曾在一次有50人参加的集会上听过他们的发言,虽然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但张泽厚心里明白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他决心用创办文艺刊物来作为自己的战斗方式。他邀约老师沈学诚与他一起合办《文艺评论》杂志。可是刊物没出几期就被政府当局查封了。后来他又独自创办了《艺术导报》、《读书月报》两份杂志。《艺术导报》刚出一期又被上海当局查封了。
1931年6月的一天晚上,张泽厚从“左联”作家高明家里出来后,在法租界被巡捕抓走,关进了巡捕房。原因是当时从他身上搜出了几本《红黑》、《小说月报》旧杂志而被怀疑是共党嫌犯。高明得知张泽厚被捕后,立即展开营救。他找到哥哥高律师设法保释。高律师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律师,神通广大,他请出青帮老大杜月笙出面担保,顺利地将张泽厚保释出来。就这样张泽厚还是被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地下室关押了一个月。这是继1930年6月在成都坐牢后他第二次牢狱之灾。对于象张泽厚这样的“左联”作家的遭遇,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己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己腐烂到连“为艺术而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鲁迅先生的结论充分肯定了“左联”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左联”作家的战斗精神,也客观地反映了“左联”作家当时的险恶处境。
张泽厚出狱后,没有工作,谋生找事做、解决吃饭问题是当务之急。老师沈学诚介绍他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书。从1931年9月开始,张泽厚在学校讲授三门课程,成了该校的专职教授。
从1933年开始,“左联”宣传部长任白戈(1906-1986,解放后曾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四川省政协主席)成了张泽厚的直接领导,彼此联系最为密切。在任白戈的支持下,张泽厚又与老师沈学诚(1904-1940)一起创办了《文艺新地》杂志。沈学诚是张泽厚在上海受益最多的师长和最亲密的战友,他们不仅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合办刊物,而且沈学诚还在学生危难之际舍弃自己的饭碗,让给张泽厚顶替谋生。他自已另行择业谋生,1933年沈学诚更名沈西苓投身电影,成为中国30年代著名电影导演。沈西苓导演的《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乡愁》、《船家女》、《十字街头》、《中华儿女》轰动一时、充满时代气息.这些影片不仅反映了中国30年代的现实生活,而且饱含着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爱国思想,特别是他导演的《十字街头》和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标志着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张泽厚与多才多艺的沈学诚不同的是,他专注于诗歌创作,他在《文艺新地》第一期上发表长篇史诗《伟大的开始》。这部史诗热情歌颂东北人民的抗日精神,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伟大的开始》是中国现代叙事诗创作历史中的重要作品,也是“中国诗歌会”的重要艺术成就之一。长诗问世后,立即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丁玲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北斗》连续刊登多篇评论文章,充分肯定《伟大的开始》的时代意义。时至今日,这部诗作仍然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陕西师范大学王荣教授把《伟大的开始》看作是“显示当时现代叙事诗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左翼”叙事诗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受到今天学者们的赞扬,显然是有着充分理由的,这是因为“左翼作家是用生命创作文学、书写人生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们编织的文学故事中,总透出对国家、民族、人类的终极关怀,表达出对民族自立、自强的渴望,这也是他们的作品至今还有价值的内在原因。”(赵学勇、李明:《左翼文学精神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论纲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35页)。张泽厚的诗歌《伟大的开始》正是倾述了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严重关切,表达了对保家卫国、战斗在白山黑水大地上的中国军民的钦佩之情 ,抒发了对执行不抵抗政策的政府当局的无限愤慨之情。王荣教授强调指出:“张泽厚的《伟大的开始》,是一首以“九•一八”事变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作品。全诗由“愤怒的士兵”、“副座的命令”、“出兵之晨”、“战士到了昂昴溪”、“午夜偶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人类与禽兽初战”、“俘虏的释放”、“中日两方面”、“人类与禽兽再战”、“禽兽的蹂躏”、“都抡市场去”及“中国起了火”等十三章组成。其结构的庞大及创作立意的自信,由此可见一斑。诗歌以充满激情的叙述话语,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事实。批判及嘲讽了中国军队及当局所奉行的不抵抗政策,颂扬了普通士兵及民众的抗战决心。”(王荣著:《中国现代叙事诗史》第三章第1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
《伟大的开始》在创作手法上则采用了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正如王荣教授所指出的那样: “实现并形成一种诗性叙事及其叙述话语的所谓抒情与叙事的结合……。如朱自清的《毁灭》、闻一多的《七子之歌》、《醒呀》、。。。。。。老舍的《鬼曲》、葆华的《幻灭》、聂绀弩的《现制度讴歌》、张泽厚的《伟大的开始》、梅痕女士的《她的旅程》、金克木的《少年行》、田间的《中国农村底故事》等,……而其结构形式的主要艺术目的及功能指向就是要凸显并贴近“感事‘性’场面及‘特写’性抒情‘画面’,强化结构的曼衍及意境的开阔,以造成一种波澜壮阔、跳跃变幻的叙事性效果。”(王荣著:《中国现代叙事诗史》、第306页)
《伟大的开始》在读者中的巨大影响和艺术上的成功,为三十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歌指明了方向:“诗歌‘要捉住现实,歌颂新世纪的意识’,应当努力去反映当时中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要歌颂这种矛盾和他的意义,从这种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吴观章:《抒情诗的魅力》,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1月版)张泽厚正是适时地捉住现实,突出了国难当头、尖锐的民族矛盾到来之时,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的爱国壮举。
《伟大的开始》作为“中国诗歌会”作家群的代表作之一,不仅在三十年代引人注目,就是在今天的中国文学界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张泽厚和“中国诗歌会”同仁的文学成就得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秦楼月在《新诗研究》一书中指出:“三十年代的中国,国难家仇更显严重,国共两党战事不断,日本帝国主义又先后挑起了“九•一八”、 “一•二八”和“七•七”事变,终于爆发了全民族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只要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诗人,即使是在象牙塔里讨生活的诗人们,也纷纷走向街头,走向田野,走向战场在残酷而壮烈的对敌斗争中寻求自己的生存与民族的出路。于是,以《文学》、《新诗歌》、《文学季刊》等杂志为阵地,推出了臧克家、蒲风、杨骚、王亚平、柳倩、江岳浪、毕奂午、李雷、贾芝、张泽厚、邵冠群、严杰人等一批“捉住现实,具体描写”的诗人,形成了中国诗歌会群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是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民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也引起了上海政府当局的高度重视。当局立即查封了张泽厚主编的《文艺新地》并密谋对张泽厚进行抓捕。幸得四川江津聂氏兄弟通风报信,张泽厚得以逃脱。在上海当局的通缉追捕下,1933年春夏时节张泽厚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四川老家避祸。
在“左联“的两年(1931-1933),张泽厚感受到了作战士的责任、当作家的艰辛、当革命者必须付出的牺牲,他在“左联”的旗帜下参加革命活动,丝毫不感到孤独,而是感到了在这个战斗集体里,大家都是志同道合、可以互诉衷情的知心朋友。“左联”团体里人人都有着救国救民的强烈使命意识,都有着不畏艰辛、百折不回的献身精神。这些都让张泽厚感到无比的充实和满足,尽管当时环境艰苦、生活困难,他和蒋光慈等左翼作家不断受到反动文人的攻击和诬陷,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左联”犹如指路明灯一样,指明了前进方向,激发着他的创作热情,使他成为了与臧克家、蒲风、杨骚、王亚平、任钧、穆木天等人齐名的“中国诗歌会”代表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左联”的短暂经历也影响了他整整一生。
(摘自张良春、张昕宇著《张泽厚传》第四章)
- 暂无评论!
- 发表评论文章评论(共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