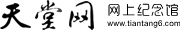——几年前有一首歌《常回家看看》唱红了祖国各地。
还 能 再 回 家 看 看 吗?
——踏访旧宅院落(之一)
2011年4月底,回国公差途中喜获良机,去“人艺”观赏话剧《蔡文姬》。与爱人乘坐地铁到了王府井站,看看时间还早,就欣然提出要回家去看看——那是我原来的家:大纱帽胡同5号。伴随着童年、少年和青年中的一段难忘光阴的院落,她自然同意了。
我与她牵手步入北京饭店的后街,“这是原来的霞公府”我乐不思蜀地介绍说。记得这些年来先后有:儿子和女儿、1位俄国博士研究生、1963年时的中学同班同学都曾经先后陪同我回家,回老宅旧院看看。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几乎完全认不得了,那时大纱帽胡同到霞公府要穿过小甜水井胡同,中间除了院落民居外,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邮电局宿舍,那里还住着东交民巷小学的同窗魏亚洲,她那时的仿宋字就是我们班公认的字模。小甜水井胡同口是座欧式宅院,曾经作为某国驻华大使馆的官邸,后来改为北京市旅游局的办公楼。胡同里在文革中增加了1座新楼,那是北京饭店的职工宿舍。而现在,这些全都无影无踪了,胡同里原有的东西、南北方向的路不见了,大街直接面临着大纱帽胡同。举起相机拍摄了大纱帽胡同1号(竟然是电脑打印出纸质的)、3号的门牌号(铁质)。
我告诉了爱人,两年前中学好友陪同我来时,在1号院遇到了小我几岁的中年男子的邻居,竟然还记得有家姓皇的曾经在5号住过,而我们自80年代中期就搬到西城去了。这次,在小院落里见到一位大妈,同样提到老米家、老皇家。她告诉我们,这里多年讲了要拆,但最终没有结果。真是难得,30来年了,他们竟然还记得,感慨的眼泪不禁在眼眶里徘徊。如果有一天他们搬走了,那就意味着这些留着童年印记的建筑一去不复返了。
按了按3号的门铃,只听得到院内的狗叫,没人来开门。是啊,自从老两口都去世了,昔日的“发小”都不愿意在这里住了。那年,俄国博士研究生陪我回来,还见到了二老。听说老人曾经在非洲某国担任过大使,这位研究华夏甲骨文的俄罗斯青年小心的问询:能否一起合影留念?许阿姨费了不小的劲儿才让米大使坐稳,那时他已经已患老年痴呆症了,对话都很困难。我们分别同米大使留影,感觉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吧。旅居万里之外,每次回国都忙忙碌碌,真的是见一次少一次!
沿着3号院的院墙拐弯,就是我们5号。
进了院儿,假山还是那座假山,可前后院的4棵每棵均为2人抱的大树早没了踪影。代之而起的是当年只有一拳粗的嫩枝,我们没有刻意去植树,都是落下的树种自然而然成长的,现在也快有1人粗了。还将那些当年只有拇指粗的枝桠长成繁茂的新树木。
当年姐姐坐在假山前那块有桌面大的石板上,潇洒的拉着手风琴,而淘气的我多少次爬到最高处,手扶着长在石缝中的树干望着蓝天白云,遐想连天。
多年前,带着儿女回来,女儿对此兴趣不大,房东不在,也没能进入屋子里。而另次刚好主人在家,他热情的邀请我们进屋,坐在昏暗的房里,怎么也想象不到,儿子3-5岁时曾经在此度过了几年的暑期。他当初还曾经玩耍在树荫下的童车里,他的爷爷戴着老花镜,边摇晃着竹制的童车边看着报纸。现在啊——该是他们开汽车了!
这次恰好是前院的房东在家,来了几次都没能到当初自己住过的屋子去看看,今年终于让我如愿以偿。文革期间,我们曾经的独门独院,又搬进来一家,将4间屋子,分隔成为2家。一家走前门,另一家走后门。日式的房屋,进门处是脱鞋的地方,木地板吱吱呀呀的,仿佛早已不堪重负。窗户框、门框已经根本见不到油漆的斑痕,而破碎的玻璃只能用报纸加胶带固定着。在这儿拍摄了屋里的状况,想象着当初冬天围着热气腾腾的火炉,烤馒头,烧开水的情形。
前院的房东同样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她们是后来换房住进来的,而当年我们第1位邻居家,因为牵扯到社会上某些纠葛,早就离此远去了。但仍还有人不断来骚扰,她们不得不请东华门派出所开具证明,确认原住户已经搬迁。我们第1位邻居家自我们搬到西城后,男主人就因病去世,后来他们家的大女儿也故去了。看来,自从他们搬进此院落,真是祸起萧墙。
在这里,前院的桑树曾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桑叶,春天我们会爬上树,摘桑叶,去喂那些白白胖胖的蚕宝宝,此时在耳边回响起在大量喂养蚕时,蚕宝宝吃桑叶时的沙沙声。夏末,吐丝的蚕为我们带来了一层又一层闪着晶莹光亮的丝棉,就别提多高兴了!院子里除了大树外,还长着些低矮的不知名的灌木,我们常去采摘些树叶,就用它们去擦洗餐具,非常干净。那时可没有现在的洗洁灵啊。夏日炎炎中,“知了”不倦地鸣叫着,3-4个星期后,蜕变的躯壳留在树上,我们摘来收集,卖到《同仁堂》中药房,每个好像是5分钱,那在当时也是笔可观的收入呐!
每年春天的星期天,爸爸妈妈带领我们翻地,我们姐弟曾经挖土种植,然后在黑黝黝的土地中播撒种子,浇水、施肥,几个月后,摘豆角、黄瓜、茄子和西红柿,那可真是汗水换来的绿色食品。记得打开化粪井的井盖,去提污水施肥,我还失手将桶掉到了污水井里,曾经后悔惭愧了许久。第二天,桶竟然在井边,是父母连夜打捞了出来。当时就想,长大后一定要像父母那样能干才行。
现在的院子里别说是土地,就是树木也不多了,因为此院距离王府井大街仅3-4分钟路,到长安街也不过5-6分钟,因此,文革中的两户增加为4户。院子里,满满的盖了不少简易的小砖房。过去的宽敞改变为拥挤,原有的土地都铺设砖块和抹上了水泥,夏、秋的蔬菜丰硕收获肯定不会再现了。
物是人非,一切好似近在眼前,又仿佛那么遥远,伴随着高楼大厦的围困,小四合院在逐渐消亡。我们都进入了耳顺之年,儿女们已经长大成人,陪伴他们的已经是完全崭新时空:电脑、网络、汽车、楼房、现代高科技、生命科学(女儿将进入“人大” 读硕)等等。而我们呢?吐着丝,留下晶莹和温暖在世间,即将像蜕变的“知了”一样,留下躯壳在世,身心会飞到另一个世界,这就足矣!还有多少次机会能回来看看呢!?
于莫斯科
2011/7/3 – 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