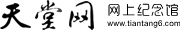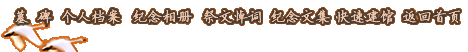军人,是父亲一生的职业。儿时,看着个子高高的父亲一身戎装,英俊潇洒、威风凛凛,心里充满了自豪和骄傲以及毫不掩饰的优越感。六岁以前随父母居住在大连金州的部队。那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是苏军进驻大连时的建筑。楼上、楼下各住两户。我们家在楼上。顶端还有一个小阁楼。记得文革初期,社会上很乱,一天深夜楼上突然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地板不停地响动,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母亲拍着我继续入睡。我害怕,睡不着。谁知一个人睡在外屋的哥哥居然调皮地跑了出去,很快就让父亲拖回屋子里。只见父亲一脸的严肃,板着脸告诉他,老老实实待在屋子里。说完就回到走廊。哥哥悄悄告诉母亲,战士们在往阁楼上运箱子。过了几天,听说地方造反派试图抢军械仓库,但是已经空空如也。枪支早已转移到我们家阁楼上。那天晚上的记忆很深刻,特别是父亲那板着的脸和异常冷峻的眼睛。父亲早年在私塾进步的王老先生引导下走上秘密的革命道路,地下侦查员的经历养成了父亲不苟言笑的性格和缜密的思维习惯。我七岁时全家随父亲调动搬到北京。那正是文革动荡时期,父亲被上调到XX部,据说履历里记载他的地下工作经历是这次调动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因素。记得有一次父亲让我去服务社给他买烟。我很快就买了回来。父亲问服务社都有什么菜,我说不知道。是呀,我直奔卖烟的柜台,哪还看其它。父亲说,顺便就看了嘛,小孩子要培养观察力。生活中父亲随时教我能力的培养和好习惯的养成。
小学三年级时我有幸考上了位于北京西郊的寄宿学校—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每个周六中午饭后回家,周日晚返回学校。我们家住在东长安街,到学校需倒两遍车。父亲只送了我一次,就开始单独往返。父亲说,以后就和小朋友们一起走吧。住校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和好朋友朝夕相处。好在大院里还有两个同伴。有时,由于各种原因只能我自己返校,父亲就教我几招“安全防身术”。比如,走路尽量在地势开阔的一边,以应付突发的意外;遇到坏人首先要冷静,寻找摆脱的机会…。不久,父亲去了寒冷的佳木斯干校。哥哥远在福建海军服役,只有我和母亲留在北京。记得冬天返校时往往一下车天已经黑了,而离学校还有长长的一段小路,路旁一边是民房,另一边则是农田。有时会遇见同校学生,有时却始终见不到一个人。有一次,好像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下车已经很晚了,我穿了一身当时很流行也很时髦的的确良军装,一下车就被一位年轻男子盯上,并主动上来搭话。问我,家里是部队的吧,说他也是,在文工团。当时路上没有其他人,他始终在跟随着我,说要和我交朋友,我心里害怕极了,想起父亲经常告诉我,遇事要冷静,便极力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只是一句话也不说。他好像看出来我的恐惧,忙解释,同学,你别害怕,我可不是坏人。后来,他聊起文工团的一些趣事,什么演《白毛女》里大春的演员把腿摔骨折啦、喜儿把辫子跳掉啦、渐渐地我的紧张和恐惧有所松弛,学校也快到了,已看到了传达室的灯光。在校门口,他停住了,说,我叫杨家林,你有空去海政文工团找我吧,一定去啊。我如释重负,连连答应。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细想,还真应该谢谢他,陪我走了这段漆黑孤独的一段路,把我送到了学校,当然后来我很快就忘了这段插曲并没有去找那个叫杨家林的人。
在外语附校读小学时母亲病危两次,我都是在课堂上被接到医院,那个时候父亲工作很忙,想想当时国家正是多事之秋,父亲他们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应对的是多么复杂的局面。在医院见到父亲时,他只对我说了两句话:要坚强,要学会自立。母亲奇迹般地两次逃离了死神的魔爪,我也变得坚强、自立。在和同学们的相处中很快就忘记了曾经的危机。在附校时的同学一直是我多年来最好的朋友。记得也是一个冬天的周六,午饭后和妞妞一起回家,因为前一天下了雪,路面很滑,我们在校门口的苏州街过马路时妞妞突然滑倒在马路中间,这时一辆大卡车迎面驶来,我毫不犹豫地上前拽她,不料连我也倒了下来,卡车在近在咫尺处刹住了,我当时仅有的思维是:完了!
可想司机有多么恼怒,冲着我们一通劈头盖脸的臭骂!妞妞站起来突然把我紧紧抱住,全然没听见司机气急败坏的喊叫,你真的太了不起啦,简直就是见义勇为的英雄!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那股勇气!
初中一年级时,有一次和妞妞去政法干校礼堂看内部电影,两部影片结束已是凌晨两点多了。任何交通工具都没有了,妞妞家很近,我却一个人从木樨地一直走到东长安街,回到家里,妈妈担心得要崩溃。其实那天夜里走在空旷的长安街,开始也充满恐惧,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男子一直在跟着我,并说带我一段路,我不理他,急急走着,大冬天的身上大汗淋漓,不仅仅是走得急,也害怕呀!
我的童年及学生时代融入了许多父亲的言传身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甚至在我这样一个女孩子也深深崇拜英雄,英雄的身世、英雄的行为,无论荆轲、项羽,还是贞德、罗兰夫人。记得小时候大院里有个游泳池,每逢夏天暑假我们大部分时间便泡在那。我无师自通地和一群孩子学会了游泳,后来在大人的指点下动作才逐步规范。都说胆子大的孩子学的快,也许是吧。我的外表一向给人文弱的印象,其实从小就喜欢和哥哥那些男孩子一起玩耍,至今留在额头上的疤痕是最有说服力的。和哥哥追跑摔得不轻啊!还有一次星期天父亲带着我,楼下的叔叔也带着他的小儿子去前门大街,回来时走到大院5号楼外围墙旁的高台时,我们两个小孩跑到上面走,结果我一脚踏空就摔了下来,足有一米多高呀,我当时的身高还不到140公分。父亲怕把我摔坏脑袋,忙送去牛街的一家脑科医院,各项检查证实完好无损,这才放心。母亲说我小的时候可真不叫父母省心!没办法,父亲的潜移默化早已使我意识道,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父辈们在战争年代视死如归、大智大勇的血,也许这就是生命最有价值的延续。
阅读(46)| 评论(0) | 编辑 |删除 |推送 |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