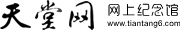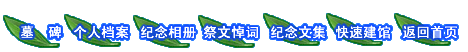外婆临走之前的一周,一直没有睡觉,护士查房,半夜,说外婆的眼睛也是睁着的。外婆摔倒后,第一次去看外婆的时候,她躺着。因为有镇静剂,没有知觉,但感觉到她有一点点的烦躁。之后去了镇静剂了,从那天开始外婆就一直醒着,从科学上说,一周不睡觉的人就应该会死。不过,我觉得那一周开始,科学应该在我外婆身上不适用了,有些东西让她一直醒着。
世界上是没有读脑波的机器的。妈妈每次做让外婆睡觉的动作,每次外婆一看见就皱眉头,是那种有点痛苦的皱眉,然后就拼命的摇头。当时我也不知道外婆为什么摇头,但回到上海,我觉得外婆一定是醒着这一周,在看这个世界,如果睡着了,她就看不见了。就这样过去了一周,外婆应该看见了好多东西,妈妈、阿姨、我、豆豆,病房和病房外的世界,现在这个不能移动的身体和过去把我们拉扯大的日子。10月5号,离开前一天,某些时刻外婆的眼神和前几天有点不一样了,眉眼低垂,有点茫然的看着前方,不在一直是那种有精力的眼神。第二天,外婆就昏迷了。
外婆对这个世界应该是有眷恋的。就从化验的指标就知道了,医生说,随便哪个指标不好都是要死人的,可外婆那几天是有几十个、可能更多的箭头,换成别人应该早就不在了。但我觉得,外婆的眷恋不是那种因为自己要死去而贪生怕死的那种眷恋,而是当生命最终审判的来临时,不服输的外婆也许在心里说:好吧,这一天终于来了,原来我以为可以让自己再多留几天的。
我们的成长就是外婆对这个世界想说的话。外公被批斗之后,学校有人贴她的大字报。小学的时候外婆就和我说:“他们贴我大字报,我根本不管他们。有些人得意洋洋,我第一把工作做好,第二我把女儿培养出来。他们得意什么,你看,现在我女儿都成才,比他们差吗?”然后,培养第三代又成为了外婆的使命,我从小学到初中都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后来,文文在外语学校初中零志愿考试中发挥失常面临被淘汰的时候,外婆又把她接管过来了。外婆管她叫小女孩,小女孩和我是外婆的第二代作品。现在想来,外婆从来没有从金钱上来衡量过自己和我们,那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在外婆对我们的教育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让子女和儿孙都成为正直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是外婆对自己和对我们的要求。还有就是,当社会在对这个家庭作出某种裁判的时刻,外婆从来没有提到过所谓“公平”二字,她的回答就是做好自己。
关于人的记忆有时候就会浓缩成一点点的细节,关于外婆最深的记忆就是幼儿园的那颗话梅糖。读幼儿园的时候每次下午外婆来接我放学,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会在外婆的办公室停留片刻,似乎也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在那里外婆会给我一颗话梅糖吃。至今,自己在放学路上满怀期待的心情和把话梅糖放入口中之后的满足感还记忆犹新,仿佛就是在昨天发生的事情。外婆是很严厉的,我有时候会鼓起胆子和外婆说再给我一颗,外婆说不行、吃多了会龋齿。我也不会再去问第二次或者撒娇,因为不会有商量的余地。只是有时候会在抽屉合拢的一霎那去看看里面到底还有多少话梅糖,关心一下自己以后的口粮。
长大之后,外婆午饭最喜欢给我做蛋炒饭和紫菜汤,而我最爱吃的则是霉干菜焐肉。还有就是下午4点我从信箱里取回来的无数报纸,做饭时留给我的背影,在学校闯了祸之后边切菜一边对我的骂声,还有深夜灯下阅读报纸时的背影。记得妈妈说,外婆每天订阅的10份报纸一定要当天看完。还记得有一次你给我说台湾的政治人物,而那时候读大学的我对这些人几乎毫无概念。
外婆走了,而我们都因为外婆长大了。我想我会常常想起外婆的。阿婆,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