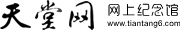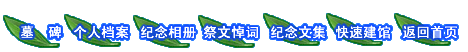腊月二十晚上,姐姐突然打来电话,说母亲不行了。我心里虽有准备,毕竟母亲92岁了。但是,我害怕听到这个消息,不相信母亲会走得这么匆忙,这么突然,我想哪怕母亲再多活10天,就过年了。
春运期间,火车票买不到,长春到呼和浩特遥遥数千里,我想买不到机票,自驾车也要赶回去。幸运,真是幸运,拨打114116购票热线,居然买到了一张,天津航空公司长春飞呼和浩特50座位的小飞机票。坐在飞机上,满脑子里都是母亲的音容笑貌,往事如五彩枫叶纷纷飘落,泪水拥着记忆在岁月的长河里流动……
母亲生我们子女8人,姐妹五人,兄弟三人,最小的姐姐6岁夭折,哥哥也在47岁时离去,白发人送黑发人,母亲的眼泪都哭干了。母亲一生经历的磨难,是常人不敢想象的。
1921年3月27日,母亲出生在吉林省柳河县柳河镇东门附近一个大户农家,外祖父兄弟三家都在一起生活。母亲最小,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18岁母亲就嫁给了父亲,祖父是柳河火车站的站长。后来父亲去日本留学,母亲与祖父母在一起生活。
母亲解放前跟随父亲去沈阳定居,走时所有东西都放在了祖父家里,只带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祖父家着了一场大火,烧光了所有的东西。1945年光复,苏联红军从满洲里进入中国,父亲和母亲正在满洲里居住,被苏联红军误当日本人抓进马迭尔电影院关了三天,出来的时候,积攒的家当连一根筷子都没剩,全被老百姓抢光了。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文革期间经常挨批斗,红卫兵跑到家里打砸抢,抄家洗劫;受父亲牵连母亲也挨过批斗,挨过打。
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家在呼和浩特,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8口人,生活非常艰难。粮食不够吃,靠代食品,麦麸子、糖菜渣子、野菜充饥。为了出去挣点钱,母亲把7岁的我和3岁的弟弟锁在家里,到别人家里去当保姆、到建筑工地扛水泥,背砖,做临时工。晚上回来,母亲看到我和弟弟满脸泪痕,相拥着睡了,母亲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母亲对我们说:“一个母亲,把自己的孩子锁在家里,去哄别人家的孩子,这种滋味比什么都难受。”
一天,我饿得难受,偷偷打开窗户,领着弟弟逃出去,跑到马路边拔“辣麻麻”野草吃,结果误吃了毒草。母亲和父亲发现我们的时候,我已经脸色铁青,口吐白沫,奄奄一息了。父亲抱着我,母亲抱着弟弟往医院跑,医院距离我家非常远,跑到医院母亲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医院的大夫说:“再晚一会儿,这孩子可就没救了。”
母亲的胆子很小,最怕的就是蛇。我们家下放农村的时候,住在一间半百年草屋里,屋顶苫房草上长满了青苔,屋檐下有燕子窝,麻雀窝,墙壁每年都得抹一层新泥,屋檐缝隙经常有毒蛇出没。有一种毒蛇当地人叫它“野鸡脖子”,蛇身上有红绿色花纹,毒性非常大,一旦被它咬伤,抢救不及时,人就会丧命。
记得有一天,一米多长的一条“野鸡脖子”从房檐钻进屋里,钻进炕上的被垛里,我看见以后大喊大叫,把母亲也吓得不知所措。毒蛇吐着红色的蛇信,又从被垛里钻出来,在炕席上游走,我吓得跳到地下,母亲急忙把我拉到她身后,她手里拿了一把小方锹,不顾一切地拍向毒蛇。因为恐惧,母亲眼睛睁得很大,但锹却没能拍到蛇,毒蛇很快就溜到了地上,母亲急忙又挥锹砍毒蛇,方锹像雨点般地落在毒蛇身上,瞬间就把毒蛇砍成数段,毒蛇在地上痉挛,母亲也瘫坐在了地上。
我长大以后,看了屠格涅夫的小说《麻雀》,原文有这样几句话:“……它是猛扑下来救护的,它以自己的躯体掩护着自己的幼儿……可是,由于恐怖,它整个小小的躯体都在颤抖,它那小小的叫声变得粗暴嘶哑了,它吓呆了,它在牺牲自己了!……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更加强大。只有依靠它, 依靠这种爱,生命才能维持下去,发展下去。”我联想到母亲砍蛇,深深地体会到这种爱,无论动物还是人,母爱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母亲一生勤劳,为了我们兄弟姊妹,每天都在不停地缝缝补补,夏天就开始给我们做棉衣棉裤,收集旧布,打浆糊,粘袼袯,纺麻绳,纳鞋底,做棉鞋。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经常在煤油灯下纳鞋底,有时我睡一觉醒了,看见母亲还在那纳鞋底,好像永远有纳不完的鞋底。
由于生活困难,常年吃不到肉。我盼望过年吃饺子,除夕的那顿饺子,最多吃过50多个,直到实在吃不下去为止。母亲每次都是只吃几个就放下筷子,微笑着看我们吃饺子。现在我理解了,母亲自己不吃,是为了让我们多吃几个饺子。
父亲去世,家里的担子落在我肩上,我到铁路当上了亦工亦农装卸工,冬天装卸火车汗水把棉裤浸透了,冷风一吹,棉裤外面冻成一层壳。回到家里,母亲坐在炉灶旁为我烤棉裤,一边烤一边流眼泪。
母亲说:“要不然咱不干了,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样下去你会累坏的。”
我说:“妈,别难受了,都是人,别人能干,我就能干。”
25岁那年,母亲为我的婚事着急,在农村与我一般大的男孩,都有对象了。母亲逢人就说:“帮我儿子介绍个对象吧!”听说邻村有个姑娘,比我小两岁,条件与我挺般配的,母亲非常高兴,赶紧与媒人约定晚上带我去相亲。
我下班回来,母亲对我说相亲的事,我对母亲说:“我这辈子也不娶媳妇了,在农村,又是黑五类子女,结了婚也会影响下一代。”
母亲怎么劝我,我也不答应,就是不去相亲。外面下着大雨,姑娘已经顶着大雨到媒人家里了,母亲没办法,顶着大雨去告诉媒人,我不相亲,母亲回来时衣服被雨全淋透了。
在我们兄弟姊妹之中,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我,我毛病太多,义气好胜,愿意打抱不平,什么朋友都交,常喝一斤多酒。有一次回呼和浩特,临走的时候母亲对我说:“记住妈的话,身体是自己的,别喝大酒,酒是最伤身体的,工作需要喝酒,也得留个心眼,能不喝,就不喝。”
我答应说:“妈,放心吧,不喝了,回去把酒戒了。”
母亲可能感觉我的回答是敷衍她,我已经走到楼外上车了,母亲又追了出来。因为她心里急,多跨了一级台阶,从台阶上跌了下来。那年母亲85岁,腿跌青了,她一瘸一拐地走到车旁,一边弯腰揉着腿,一边还不停地嘱咐我说:“听妈的话,一定要少喝酒,啊,记住,少喝酒。”
如今我也年近花甲,一想起母亲的嘱咐,想起母亲弯腰揉腿的情景,酒真就咽不下去了。
母亲长得端庄,有文化,能读书写字,唱歌也非常好听,与她同龄的人都很羡慕她。在农村生活所迫,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是,母亲也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母亲带领我们去山上割柴,下田种地。她从来不畏艰苦,不记前嫌,经常教导嘱咐我不要树立仇敌。我憎恨文革期间打过父亲和母亲的人。
母亲说:“我不恨他们,一切都是时代造成的,别看红卫兵打人,他们也是时代的牺牲品。人应该学会宽容,国家主席,总理,部长有多少比你爸官大的,不也是一样挨整,就是那个时代。”
母亲离别故乡57年后仅回去过一次,那天,我开着车,拉着75岁的母亲和80岁的大姨,还有我的女儿和儿子,一起来到柳河县城。路过钓鱼台山的时候,母亲让我把车停下来,以山为背景照了几张相。
母亲指着山对大姨说:“姐,你看,一点没变,山没变,往东走不远就是滚兔子岭了,小时候我们常去那儿采山菜,采蘑菇。”
到火车站前,母亲又指着车站说:“姐,车站还是那个车站,没变,快60年了,车站还是那个样儿。”
到柳河街里大街小巷开车转了几圈,母亲说:“别转了,走吧,这街里变化太大了,东门没有了,啥也没有了。但是,小时候的事,全都记得,怎么就像是昨天的事呢。”
大姨家在吉林市,母亲来我家,大姨也来陪母亲一起住了八个多月,俩人在一起非常高兴,每天都是开心的笑声,两人长得很像,都是满头银发,白白胖胖,一脸慈祥。走在街上,经常有人问:“是老姐俩吧?长得真像,真羡慕你们。”
母亲会吸烟,在我家里住了两年,把烟戒了。原因很简单,有一天,我开工资,给母亲买了两条高档一点的烟,我是想让母亲高兴,没想到她却不高兴了。
母亲说:“本来吸烟就没什么用,也没好处,我早就想戒了,你花那么多钱,给我买烟,我心里不得劲,从今天开始,我把戒烟了。”
母亲说到做到,从那天以后再也没吸烟,现在想起来,我心里还隐隐地痛,母亲没有更多的爱好,只是吸一点烟,不是很多,一天吸一两支,因为我不小心,母亲还把烟戒了。
母亲不信佛,从来没见过母亲烧香拜佛,甚至到祖父母和父亲的坟前,也没听母亲说一句祈祷,许愿之类的话。也许是看《西游记》电视剧的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吧,母亲80岁的时候,喜欢观世音菩萨了,脖子上戴了一个做工很粗糙的玉观音,仅此而已,从来不做礼拜、摆供品、烧香、叩拜之类的事。
母亲走了,没给我们留下遗产,也没留下债务,也没留下一句遗言。母亲对人生有独到见解,平日里她常说:“可能与我个人经历有关,人活着就得靠自己,第一是身体,没有好的身体,什么事也做不了。”
妹妹说:“母亲和父亲一样是坐着走的,一脸的安祥,悄无声息地去了天堂。”
成语里有人间天堂和人间地狱之说,至于天上的天堂,母亲不信,父亲不信,我也不信。但是,因为母亲在人间经受的磨难太多,操劳太多,我真希望因母亲而有天堂。
我在网上找到了天堂网,里面有一首歌《慈祥的母亲》,有几句歌词:“我慈祥的母亲是美人中的美人…是儿女们的太阳…我是你用生命写下的历史…
母亲最爱听我们给她唱歌,如今,母亲听不到我们的歌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弟弟说:“如果母亲不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活到100岁没有问题。”我赞同弟弟的观点。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临行时我带上一张母亲的遗像,一块白布孝带留做纪念。
大姐说:“咱家那个大银勺子是苏联红军送给父亲的,咱家经历这么多劫难,它还能幸存下来,有意义的东西就剩这个大银勺子了,你带上吧,留个纪念。”
二姐、三姐、妹妹、都让我带上银勺子。睹物思亲,一把银勺子是一部浩劫的家史,是一首颠簸流离的长恨歌。
我坐在电脑前,打开天堂网母亲纪念馆,面对母亲的微笑,一遍又一遍地听《慈祥的母亲》,最爱听那句我慈祥的母亲是美人中的美人…是儿女们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