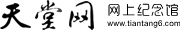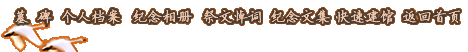写在前面:今天是农历的六月初六,是祖父和父亲共同的祭日。又是烟雨天,天也哭地也颤。何以解思念,唯有这泪水般的雨呀泪连连。
一篇旧作,贴在天堂网的墓前。感念祖恩,永远怀念!
一世情缘 ——纪念慈父斗南子(王其学)先生诞辰七十年
作者 梨花烟雨 阅读:5028 发表江山文学网
时间2011-08-27
思绪在梦境里延展,我梦见父亲复活了,我好像是在看一副画面,看着看着那幅画便活了起来。画里面小桥流水,杨柳婀娜,远山轻罩着几痕雾紫,仿佛润朗着“紫气东来”的仙气。有人在桥上憧憧来往,走在最后面的便是我那朝思暮想的父亲。父亲似乎比活着时矮了许多,却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清癯的脸上含漾着春晓朝梦般的无限春意,全然一副仙风道骨的悠闲神情,只一晃就不见了。
晨风吹断了清梦,像一个电影的镜头,掠过无痕。父亲啊父亲,您真的化仙而去了么?是吗?
我轻轻取出父亲的遗照,沉甸甸地摆放在儿子的书柜、窗口、书桌,举起相机,为父亲拍下异国他乡的第一组照片。算是让父亲的魂灵同我们一起在遥远的俄罗斯安下个临时的家。说好儿子毕业时带父母一起来参加毕业典礼的,父亲也是满口答应好的。可现在,一切都不存在了,那个美梦过早的破灭了,如电光闪灭,水泡破裂,梦想有多美好,现实便有多残酷。
儿子瞥见了我拍照的全过程——虽然我是悄悄的、敏捷的、不愿惊扰任何人的,心里的悲哀不想带给任何人,丧父之痛只想自己默默承受,在心灵的一隅独自舔舐伤口。但我一抬头,却看到了儿子书柜上的另一幅照片,是他与我父亲的合影。去年暑假,儿子有幸见到了姥爷最后一面,并参加了姥爷的丧礼,返校时带了这张他们爷孙俩的合影,摆在书柜里,时时感念姥爷的恩德。他是第三代最大的孩子,也是得到姥爷恩惠最多的孩子。他们不仅是爷孙,也是文友,更是交心的忘年之交的挚友。父亲厚地高天的恩德,哪个儿孙不感念?哪个亲人不心痛!
“把姥爷的照片给我留下吧。”儿子不动声色地说,但嗓音里分明有些沉重。我尽量平静地答道:“好,走时再留吧。我走之前,要让姥爷随我游遍所有我经过的地方。活着不能了,心到神知吧。我和你爸都来了,家里没人,我不能把姥爷一个人留在家里,无人供奉,天又热。虽然正式的灵台在姥姥那边,可我总觉得姥爷无处不在,他已随我来了……”我再也说不下去,哽咽着迅疾离开了儿子房间。
父亲没了,家也亡了,连儿子都发出了“家破人亡”的凄号,父亲这棵大树,说枯就枯了,连根拔起,瞬时化为灰烬。父亲生前曾说,我是他早年间种下的一颗小树苗,父亲用他多年的心血精心浇灌着。小树苗在父亲的呵护中渐渐长大,开花结果,在盛夏也有了一片小小的绿荫,也能供父亲来纳一会儿凉,女儿也能将一半个果子奉呈了。当这棵树再长大些,结的果子再多些了,父亲却再也不能来了,永远都不来了!
父亲啊父亲,铄石流金的六月天,却成了儿女一身重孝无尽的悲凉和寒冷。您走在一个深夜,不让太阳看到您不舍儿女们的无奈和爱恋;您走在一个雨夜,不让月亮看到你我的泪眼悲叹和载不动的遗憾;您走在我的暑假,我有的是时间哭你念你忆你读你。现身在异域,也毫无背井离乡之感,一个失掉家园的孤魂,走到哪里都没有家,从此浪迹天涯。
我将父亲的灵台设在了我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备了简单的供品。我带着父亲的灵台走遍四方。列宁广场、中心花园、电影院内、话剧剧场、步行街、州政府,斯娃达朋友的生日Parte夜总会、巴维尔先生的森林训练基地、金碧辉煌的教堂前,大森林中、白桦树下、草原之间、奥噶河畔,都与父亲共同走过。父亲是有灵感的,总在关键时刻给我佑助,比如我们看3D电影和在纪念碑前时均感到饥肠辘辘,父亲如他活着时一样的慷慨解囊,没想到,给父亲备的供品成了我们暂时充饥的食粮。我们亦如吃上坟时的供品,虔诚而感念,且适可而止,从不敢将供品全部消纳。
站在奥噶河桥头,看桥下的风景,中国的酷夏,在俄罗斯却是柳暗花明处,江河满目春。碧蓝的天空浮动着座座雪山似的白云,杨柳依依,双堤画水,一群野鸭悠闲自在的在水面上畅游嬉戏,在清波里依洄,或啄食,或求偶;也有的在岸上,卧在绿草丛里栖息,疏疏落落点缀在草坪上、水藻尖,像一只只晶亮的贝壳。梅花鹿伸着长颈静看流云,三两只天鹅曲颈高歌,十几只彩鸽在阳光下扑闪着孔雀蓝的翅膀,在草地上觅食。忽然,岸边的环河路上响起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一对巡警骑着高头大马在巡逻。灰色制服在媚光里随着马蹄声上下起伏,威风凛凛的沿街而过。
奥噶河畔矗立着百米高的纪念碑,用俄文正楷浮雕着奥廖尔城的历史简介,也是市中心的标志。碑的四周鲜花铺地,连接着碧绿的草坪,依依的桥栏,栏下是汩汩流淌的奥噶河水。我不禁拿出父亲的遗照,像他生前一样跟他来一张合影,彩照里的父亲仍然慈祥的看着我,但当我将父亲的照片捧在胸前的一霎那,却再一次心痛的知道:父亲的确已经不在了。当儿子对着我们父女按动快门时,极力想给父亲一个笑容的我终是没有笑出来。
在这向晚的夏末,伫立桥头,望着远方苍绿的大森林,每一棵白桦树都直耸云端,株株冲着天心,融化在蓝天白云之间;森林的绿意逶迤而来,层次分明的飘摇着白茫茫、黄灿灿的野花,一片连着一片,铺向碧绿的草原,一望无际,也更迷人眼。欧式建筑的A字形楼顶、月洞窗口、树梢上、草丛里,上上上下下栖着乌鸦,伸着尖喙在青草花圃里觅食,或在屋宇上倦盹。凝望着奥噶河水,饱览这美景如画,心中不免感慨万千,心湖激荡,俄罗斯的天地风情之于已逝的父亲算不算稀奇?算不算美好?九寨沟一步一景的大观是否抵得过异国他乡的风情如画?想父亲缘何这样无寿无福,为什么不能再多活几年,跟女儿来这异域走一走,看一看。您观过的九寨沟风光,怎抵得过您为儿女们挡风遮雨的一世辛劳;您游过的长江黄河,怎抵得过您对我们付出的爱与心血;壶口瀑布的汹涌,怎抵得过儿女们对您的滔滔思念和感恩。难道父亲来世上走这一遭,就只是为了奉献和付出吗?难道这也是上天安排好的吗?
现在人是没了,西墙已度,魂归来处。天上人间,却依旧痴迷。凝望苍穹,再投下一眼迷离的期盼,依稀看见你仙影翩翩,向我飘来。父亲的灵魂在天上看着我,我也仰望着父亲,相对无言。我们与父亲这一世的情缘已恍如隔世,再不能享。不敢往后看,但只回眸一瞥,那四十七年的光景已是千像万影,憧憧无余地铺满眼迹,一幕一幕循环映着,流连忘返又不忍相看。回忆的繁华树上越是热闹非凡,越是显得凄凄凉凉。
父亲去世后,许多人扼腕叹息,为他的早逝,为他的太过辛劳,这是人情,令我感念和温暖。也有人不赞成父亲太执着于文学梦,太痴迷于他的理想,甚至有人要以此为戒,好在世上多活几天。对于这个问题,我经常暗暗思索,父亲这一生到底值不值?再给他几十年的寿命,他就可以饱食终日,碌碌无为的活吗?答案是否定的。父亲追求梦想,实现人生价值,就如彩蛾永远不能忘情于火焰一般,即使粉身碎骨,化为灰烬,哪怕只有萤火一点微光,也要将光焰喷薄,留点东西给儿孙,给社会。可以使后代引以为豪,证见先辈的存在,识得先辈的价值,有宝贵的东西值得他们珍藏、爱慕和纪念。即使生命再短促一点,或者再长久一些,我相信,父亲依旧还会这么活着。有些人生永远不被人理解和赞同,宛如山下的矮树,永远体会不到山巅吞吐上挽碧空的岫云那份悠然自得、大气磅礴一样,他的快乐是在追赶光芒万丈的日月星辰。
生命的终结是每个人的结局,只是来早与来迟。人生只是个机缘巧合,日子河水般汤汤流着,谁都不知道哪一天就轮着自己被运神摆布,再也躲不开,匆遽中给潜藏在水底的涡流卷了去。幻壳被消灭是人生命定的结局。如阿拉丁的神灯,只能喷薄瞬间的流彩,不能永远临照。寿命也不能代表一切,我亲见许多个生命在纸醉金迷里,在醉生梦死里荒废;许多个生命在勾心斗角里,在无聊透顶里沉浸,他们似乎是被无形的魔力蛊定了的,比如一粒蒸不透的珍珠米,性灵的光辉永远离别了沸腾的波心。精神的穷乏才是最悲哀的,灵魂的堕落才是最可耻的。凡物各尽其性,即使一一棵小草,只要沐得一丝阳光,浴得一滴甘露,也要致力完展仅有的叶片,尽情倾吐所有的绿意;一只夜萤,哪怕顷刻间死去,也要飞过丛林,穿越草莽,为世界发出哪怕微弱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光芒。何况是人。无论穿的是锦衣还是贱麻,吃的是御食还是薯饼,都阻挡不住灵府魂蛾的展翅高翔。高翔——高翔,即使那理想如天边月,云中星,化成灰也要奔放——奔放。
“人生是辛苦的,最辛苦的是那些在茫茫天地间寻求光热的生灵,可怜的秋蛾,他永远不能忘情于火焰。在泥草间化生,在黑暗里飞行,抖擞着翅羽上的金粉——它的愿望是万万星外的一颗星。那就是我。见到光就感到激奋,见着光就顾不得粉脆的躯体,见着光就满身充满着悲惨的神异,殉献的奇丽——到火焰的底里去实现生命的意义。那就是我。”这是徐志摩的话,他自己也只在世上活了34岁,但他至今活着,他的诗魂的魅力之花永远在世间绽放。多少年轻人至今还被他的文字熏陶着,迷恋着,汲取着他诗文里的营养。他在他的散文《话》里说:“只要在有生的期间内,将天赋可能的个性尽情的实现,就是造化旨意的完成。”这也是他短促一生的真实写照;济慈虽然二十五岁作古,但他的夜莺却从古唱到今,让后人沉醴般浸醉在他夜莺的馥郁里。济慈这句说得更好:“不像是叶子那么长上树枝,那还不如不来的好。”
父亲在他的诗里说作为人是“长苦辛”,但他终其一生都像慕光明的花蛾,在黑暗里扑捉着火焰的彩光和晴霞。一直写呀写呀,直到最后的时光,也总是要“留下点什么”。多少年来,父亲就一直在冥冥之中为着离世的一天做着准备。只是不知道这一天来得这样迅猛,这样猝不及防,这样赶早。因为他还没写够,没爱够,没奉献够。我想,现如今,也许如他的网络昵称“斗南子”一般,父亲已经化作了天上的斗南星,依然竭力散发着自己微弱的光辉,为浩渺的寰宇增一媚微霞。父亲一生勤苦,忙碌一世,与我们在凡尘的这一世缘分终是尽了。不幸的同时,又在想,我还是幸运的成为了父亲的女儿,又幸运的成为父亲的第一个孩子,如我儿子所钦羡我甚至含点妒嫉醋意的那句话:“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姥爷陪了你半辈子了,你是他生的,我就没你那么幸运……”
罗曼罗兰说:“我们应得感悟到生命最伟大,最生产——甚至最快乐是在受苦痛的时候”;歌德说的——和着悲哀吞他的饭,谁不曾拥着半夜的孤衾饮泣?现在父亲再也不用劳烦了,骤离了这尘世蹂烂的坑道儿,任何风雨都吹打不到他了。他用他的死获得了永生,赢得了永恒的自由和宁静。这个世上的扰攘早已与他无关,大劫难中的大圆觉,大悲剧中的大解脱。
我们与父亲这一世情缘是幸运的,也是弥足珍贵的。梦里的世界、回忆的亭榭没有围墙,父亲经常慈祥地在梦里,在回忆里向我走来,一刻不曾离开我。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的死渐行渐远,父亲的生却犹在眼前。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殷殷的在眼前浮现。回忆的长廊里舞蹈着快乐的音符,有父亲的往事总是繁花似锦,流光溢彩的。虽然父亲经常说自己只是“一介草民”,但他无愧于他的一生,无愧于他的祖先与后裔,他的文字将永远浇灌着他的后代子孙们茁壮成长,他精神的辉煌光芒也必将照彻我们前路的迷茫和幽暗。父亲用他的死,让我们些许体会到生的意义,死的价值,悟出一点生死之间一丝缕幽玄的消息,尘世是喧嚣纷呶的,也是坎坷颠顿的,但您的后辈们却永久存储铭记你不朽的灵光,永远坚韧的续走您光明的坦途。
由于机票的原因,女儿已经不能回国给父亲过“七十大寿”了,但父亲始终与我同在,况,父亲生前欣赏毛泽东那句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现在科技发达,信息畅通,无论国内国外,打开计算机,便可以搜索到父亲“斗南子(王其学)”的博客及各个文学网站的文章,父亲走的只是躯壳,而精神不死,文字永生。“七十大寿”这一天,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国内国外,在您的遗照前,父亲的亡魂必将被所有的儿孙们深切的怀念和祭奠。
写在父亲诞辰七十年之际,愿父亲的灵魂安息!
2011-8-26于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