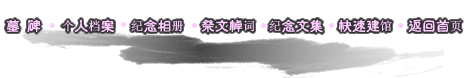一、应国家急需创办石油地质专业
新中国建立伊始,人民欢庆,百废俱兴,然而各项物资,特别是石油能源奇缺(当时我国仅有延长、玉门两个油矿及四川一个小气矿,49年原油总产量只有12万吨)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的回复和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尽快培养一大批年轻的石油地质专业人员,以便对石油资源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与勘探。另外,在我国尽早找到新油田,特别是大油田,也是对鼓吹“中国贫油”“中国主要是陆相盆地,不可能生成大量石油”论调的强有力驳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大学地质系先是应西北石油局的邀请,于1950年8月开始在国内创办定向培养石油地质人才的速成训练班,招收了50多个学生,他们于52年毕业后,除个别人留校任教(祝总棋)外,大都分配到祖国最需要和最艰苦的大西北做石油的调查与勘探工作,他们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仅是良好的开始,而调查与勘探石油的任务还很多很大,急需的石油地质人员还很多很多。为了配合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燃化部和地质部根据正在酝酿中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精神,向教育部提出请求,希望能尽快高质量培养一大批年轻的地质人员,去从事石油和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勘探。教育部立即在1951年上半年召开的“培养地质干部座谈会”上提出,希望由两三所具有条件的大学,筹建石油地质专业,与原有的矿产地质专业共同来承担这项光荣任务。然而各院校到会代表均感到困难很大,“每年要招四、五百学生,连续三年,怎么承担得起”。当时西北大学参加会议的张伯声教授认为这确实是国家急需,应想办法去完成,同时这也是发展壮大西北大学地质系的很好机会,便挺身陈词,摆出了我们学校地处当时找油找矿的重点地区-大西北,西大地质系又正在为西北石油局培养一批二年制石油地质人才的速成训练班,共50多个学生,已积累了一些办学经验,愿意承担两部提出的任务。就这样西北大学地质系按前苏联有关专业教学计划筹建石油地质专业,并于1952年首次大规模招该专业学生200人,同时也招矿产地质专业学生200人,53、54年石油地质专业又各招200人(西大一年的成功实践,引起了兄弟院校的羡慕,他们也主动向教育部请缨,加之北京地质学院已经成立,53、54年教育部已不再给西大下达矿产地质专业的招生任务),这样三年共完成了培养地质人才800人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放西北大学旧校门-纪念册p.176下图或另选及张伯声老师年轻时照片各一张)
二、办学过程
张伯声教授领回的这项重大任务,一度受到了学校一部分人的责难,认为到时候完不成任务看怎么交代?在这种情况下,张主任召开了全系大会,让大家集思广益,出主意、想办法,大家认为任务来的太突然,困难确实很大,部分人的担忧也有一定道理,但只要全系上下团结一心,把困难想够,一个一个设法克服,总会胜利完成国家交给的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的。
经过仔细分析,当时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三:一是52年一次招收400学生(石油地质专业200、矿产地质专业200)确实很多;二是全系教师有限(不超过10人),且都是教基础地质的;三是两年如何按前苏联石油地质专业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心中无数。 1、师资问题
在上述困难中,师资队伍的困难是首要的,也卽是其中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的也就容易解决。
不足10位教师要应对首次入学的400学生,单从数量上看明显是不足的,当时采取的办法,一是由张伯声和郁士元二位老先生出面四处联系,争取了有名望的地质学家,教授,和老校友来系专职或兼职任教,先后来校的有王永焱,袁耀庭,夏开儒,张更,关恩威等老师;二是从外校请进了一批应届大学毕业生担任助教,如剪万筹,刘孝忠,汤锡元,陈荷立,丘燕昌,何开华,杨训庭,胡德绥等;三是本系与外系毕业生或提前结业生留校任助教,如高焕章,陈润业,赵重远,王永华,安三元,陈景维,陆岩,郭勇岭,王俊发,李建,薛福海,祝总祺等;四是从当时的咸阳西北工学院有针对性地聘请了一些工程课老师,如采油工程,机械制图等的老师;五是普通基础课,包括数理化,政治,体育等由学校有关系和教研室老师承担.
通过上述办法,教师数量明显增加,但教师的业务水平必须迅速提高以便担起教课任务,当时老师们首先碰到的是教材和有关参考资料以及教学大纲问题,解放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欧美的教材等,特别是专业教材根本无法得到,能看到的都是前苏联的,因此,要提高业务水平,当务之急是先突击学俄文,在这方面张伯声老师起到了表率作用,年已半百的他,坚持学习五个月就能阅读专业书刊了,而且在学习过程中还翻译出版了奥布鲁切夫的<地质学原理>,其他老师先后也都达到或接近这个水平.为适应苏联石油地质专业教学计划规定课程的需求,还必须对老师们的教学进行通盘考虑全面安排,基础地质类课程,都由原有老师承担,他们业务基础扎实,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完全可以保证教学质量,只是学生太多必须大班讲课小组实习(200人分四个班,讲课多是两个班在一起,实习课一般一个班分成四个小组进行,实习课主讲老师有时也来,主要由配备的年青助教上课),新开的专业课分别都由分来的和留校的年青教师承担,这些课都是第二学年的课,至少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备课,其中一些老师还被立即派出去进修,如51,52年先后派出去的有,陈润业老师去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进修古植物学,赵重远老师去玉门油矿进修钻井地质学,祝总祺老师专门向张更教授学习石油地质学,高焕章和薛福海老师去东北分别向苏联专家学习物探和测井地质学等.通过提前备课和派出进修,年青老师们也都能比较满意地担起了有关课程的教学,其中有的老师还提前编出了成本教材,使教学效果更明显提高.
(放纪念册p.170中图、p.177中图及177下图)
2,学生状况
1952年考入西北大学地质系的400名学生,都是按大学四年制本科生录取发的通知书,进校后突然改成两年专修科,最初校系领导担心学生会不同意,甚至会闹起来,谁知经领导说明国家的急需后,除个别人要求转系外,绝大多数都接受了新的安排.国家急需确实是大家同意校方意见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与当时大多数学生家庭都比较困难,看到能上大学而且吃住不要钱,已经非常满意了/另外,考虑到提前两年毕业还可以早拿工资补助家庭。这400人来自全国各地,但主要来自西北和西南地区,后两个地区的学生全是集体入校的,记得很清楚,西北地区的学生是集体从兰州乘刚开通的兰州-西安的第一趟火车来校的,因为是第一趟开通火车,人很挤,秩序也非常乱,致使一些人到了西安,行李却丢到了宝鸡,不得不再去找行李.西南来的学生,是几十辆卡车浩浩荡荡翻过秦岭先拉到宝鸡,再乘火车到西安的.
( 放400人珍贵长照片)
解放前西大地质系和国内其他院校地质系一样,每年只招几个学生,很少超过十个人的,如上所述,1952年一次入校的就是400人,它相当于解放前的40倍,与西大1950年首次招的石油地质速成训练班的50多学生比,其人数也超过了8倍.不仅学生人数突增很多,更重要的是虽然他们的主流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都是按第一志愿录取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但总体上不论从生活习惯,年龄结构及业务基础上看,这个群体仍存在着明显差异.就生活习惯来说,西大处在我国北方,以吃面食为主,气候干躁,风沙大,冬季特冷,当时基本没有取暖条件,夏天又比较酷热,而洗澡条件又不太好,南方(包括西南)来的同学一开始必然不很适应,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产生一些思想波动;以年龄看,该群体学生一般是20岁左右,小的只有16-17岁,也有相当一些是24-25岁,还有几个同学是1918年出生的,当时的年龄已是34岁了;从业务基础看,除应届高中毕业生为其主体外,也有不少解放军和在职干部经过1-2年速成中学学习后分配来校的,还有一些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而后复员转业推荐来上学的.无疑,这些差别所引起的思想,爱好和业务基础的差异,必然会给管理和教学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因之,要教好这些学生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教学安排
这批学生入学后.基本都有助学金,家庭困难大些的助学金还要高些,最低助学金也够吃饭用,因之,大家的吃住实际都是国家包了的.一些同学,特别是南方来的同学,在生活或其他方面遇到些困难,思想有些波动时,学校专门给各班配有政治辅导员,除作思想工作外,更多的是帮大家解决具体困难,如冬天很冷,立即给北方特困及南方多数同学补助棉衣棉裤及棉被,伙食同时开了米灶,面灶及清真灶,同学们愿意吃啥都随意.医疗都是免费的,一些有病的同学,还辟有专门住宿区,以保证他们很好休息,以便早日恢复健康.两年中同学们不论思想,生活和其他方面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向辅导员反映,及时得到他们的帮助,因此,在这段时间大家生活的非常愉快.
当时遇到最多的困难还是教学问题,一是当时采用的是四或五年制苏联石油地质专业教学计划,不包括野外实习,室内教学的课程就有30多门,要我们在两年内全部学完,不得不上,下午8节课全排满(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对二年制石油地质专业学生来说,一些课如机械制图,保安技术,电工学,采油工程等都至少暂时可以不上);二是专业上的快,学生又突增很多,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虽想尽办法让他们备好课,他们也确实尽了最大努力,也比较满意的开出了课,但如前所述,除个别人课前编出成本教材外,都是自己先学一点,编一点,再教给学生一点,同学们主要靠课堂记笔记来学习.这样程度高的同学跟得上,而基础差的同学,特别是年龄偏大些的同学根本赶不上,教与学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保证所有同学都能学到手,当时系上采用了两种措施,一是所有课程都在学生中确定一名课代表,其主要任务是了解同学学习情况和向老师反映那些讲的不透,那些同学学习有困难,以便老师在之后的教学中改进及进一步辅导同学时参考;二是强调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发扬互助友爱精神,老师在难点处多重复讲解,课后多辅导一些,绝大多数老师,特别是年青老师晚饭后大都在办公室备课,帮助随时来问问题的同学,对一些普遍难懂的问题,主讲老师甚至在大礼堂对所有学生进行讲解;同学之间,开展一帮一,甚至二帮一的活动.这种团结友爱的精神,大大激发了同学们顽强奋斗,刻苦学习的热情.
野外实习是地质专业,当然也是石油地质专业非常重要的教学环节,限于两年的学制仅安排了两次,都是在一年级室内教学结束后进行的,先安排的是地质实习,似乎是一个半月,从铜川到焦坪等地,几乎观察了我国北方奥陶纪至第三纪的全套地层,看到和识别了断层,,褶皱等构造现象,找到了几类化石,知道了它们在确定地层时代上的重要性.还去四郎庙石油探区参观学习,据该探区技术人员介绍四郎庙三叠纪地层是一个宽缓背斜构造,探井就布在构造高点上,技术员还带我们看了他们的钻井及简易化验室,使我们粗浅的知道了一些录井工作.(当时我们还未上专业课).我们这次实习都是步行,配有医生及专门负责后勤联络和炊事的工作人员,共200多人,分十多个小组分别由老师带领边讲边看.,这次的实习收获很大.对我们在二年级时学习专业课十分有用。接着用两周左右的时间去临潼进行测量实习,主要是如何测量方向,距离,高程及测绘地形图,当然也包括在地形图上定点等.这些对我们之后填地质图十分有用.学习测绘的同时,大家还顺便第一次游览了华清池风景区,这次实习大家也非常满意。两次实习几乎把暑假全占用了,但同学们并无任何怨言。
(放p.173下图、175上和中图、171下图)
二年级课上完后应安排一次专业实习,限于时间就把它跟毕业分配后的工作结合起来了,没有再单独安排.
, 与现时教学安排相比,这种全负荷的安排是否影响了同学们的德育和体育的培养?事实说明也并不如此,关键是看你对这两方面抓不抓,安排得如何.在两年紧张学习中老师的无私辅导及同学间的相互帮助,潜移默化的培养了同学们良好的道德品质,如有的同学见一位老师家庭生活有些困难,就主动无偿资助。校系对体育锻炼丝毫也没有放松,每天大家都是定时起床,洗漱完后,共同做操,在宿舍门前自制的简易单杠上拉引体向上,或在地上作伏卧撑,记忆中乙班的李文彬同学引体向上和俯卧撑的成绩都是最优秀的,每次似乎不费劲的就可以拉十几至二十几下。下午的课外活动一般都得跑步或参加球类活动.当时的地质系男,女生排球队在全校都是领先的,校男排球队成员,地质系的学生占大多数,该队在省市比赛中还取得了较好的名次.叶俭同学的短跑很出众,53年她还代表西北局参加了全运会选拔赛.文艺活动也组织大家踊跃参加,但一般只放在节假日,如礼拜六很多同学去大礼堂跳友谊舞,愉快,活燿得很。
(放170下图、173上图和中图)
. 三.毕业分配
原来四年的计划两年完成后,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指导思想下,毕业分配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同学们争着去最艰苦的大西北.事实上当时的大西北确实是调查与勘探石油的首选或主要战场,国家为什么当时要单设一个西北石油局也是根据当时的需要出发的, 正是出于这一点,分配中除几个同学分到广东茂名和广西百色,从事油页岩等工作,少数同学直接分到延长和玉门两个油矿及四川一个气矿外,绝大部分同学都分到西北石油局与新疆中苏石油公司(即现在的新疆石油管理局)。
前者约占石油地质专业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后者大致是四分之一。分到西北石油局的同学立即再分到大西北的土鲁番、柴达木、酒泉、潮水、阿拉善、陕北、内蒙等许多野外队,每个地方分去的同学也就是几个人,最多十几个人。按每个地方去的人数多少算,新疆是最多的,这是因为第一、它是前苏联援助和合作的单位,有许多苏联各路专家,要向他们取经学习,如之后转到全国各油田的叶得泉、李应培、蒋显庭、蔡治国、唐文松、赖星蓉、张兴暻等古介形虫专家,都是当时在该公司进行有关专业学习的;第二、当时新疆发现不少油气显示,很需要花大力气首先调查与勘探;第三、苏联专家毕竟人数有限,很需要我们的专业人员配合他们工作,记得我们刚到该公司时,因为缺乏石油地质人员,不得不把天津大学学化工的一些学生安排跟苏联专家一起工作。去新疆的这批同学由当时初定留校去该公司向苏联专家学习一年的邸世祥和叶俭带队前往的。54年5月底分配到新疆中苏石油公司四十多人,高唱着前苏联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吻别你的儿子吧…….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之歌离开母校。我们是先乘火车由西安到兰州(当时火车只通到兰州)接着坐两辆敞篷汽车向新疆出发。同学们由于当时这一带路基很差加之所坐卡车比较破旧,车速很慢,致使我们从兰州-乌鲁木齐尽然花了十天时间。和同学们共处的十天中,虽然沿途自然环境越来越差,河西走廊还可以看到一些绿色,出了嘉峪关及更远的乌梢岭以西,则是寸草不生的沙漠和戈壁滩,但大家的情绪并没有变坏,而是越来越团结,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每天上车时,不是争着坐车前,而是都想坐车屁股,幽默点说,是为了领略到开车时沙尘扑头盖脸,下车时泥土人站在面前的情景,每晚下车后,又总是把较好的房间和床位让给女同学和年纪较大的同学。出了甘肃安西城,前面就是无垠的戈壁,中午时分在汽车前进的右侧方向,突然看到碧波荡漾水面,同学们齐声大喊“好美啊”!施一同学下车向美丽的景色跑去,一会儿便有同学醒悟过来,大喊“快回来!别跑了,是海市盛楼”。一路上谈笑与歌声一直不断,唱的最多的是“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内心,建设祖国当先锋”,谈论得最多的是路途见闻,如对兰州黄河水面上的羊皮筏子认为这太危险,但亲自坐了一下,就认识到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过度工具,一个人就轻便地扛走了,坐上去很平稳,并不危险。离校时学校发给每一个同学发一顶草帽,很多同学的草帽都被风吹走了,大家还都笑称“没有学好郁士元老师讲的安全保护课”。在哈密看到放学后河边不时有小朋友唱歌跳舞的群体,立即意识到维吾尔族不愧为一个豪放能歌善舞的民族。见到大片沙漠、戈壁滩后,深感这么大的土地不能利用,实在太可惜了,盼望科学尽快发展能对它们进行改造,有些还谈到,在这些地方,找到油气田该多好,那时它也将成为美丽的石油城。
(放179中图和下图180上图202上图和中上及中下)
1954年6月14日到乌鲁木齐报到后大部分同学分配到南北疆地质队和钻井队。北疆有宋汉良、毛希森、王世仁、朱瑞明等;南疆有王志武、雍天寿、靳仰廉、桂明义、陶瑞明、林积桐、王秋明等;杨汝朴、唐文松、郝服光、刘克诚、何武魁、张工、李培勤分配到乌鲁木齐化验室。记的到乌鲁木齐的第二天,一看太阳升起来,同学们按学校习惯都起来跑早操,早操后6点多了大家都纳闷街面上还是没什么人,才明白新疆与内地有2个小时时差,这是同学们来疆第一次倒时差。大家三天内分别被安排了新的岗位,开始了新的学习和工作,我和叶俭在该公司不同单位进修一年后又回到了学校。